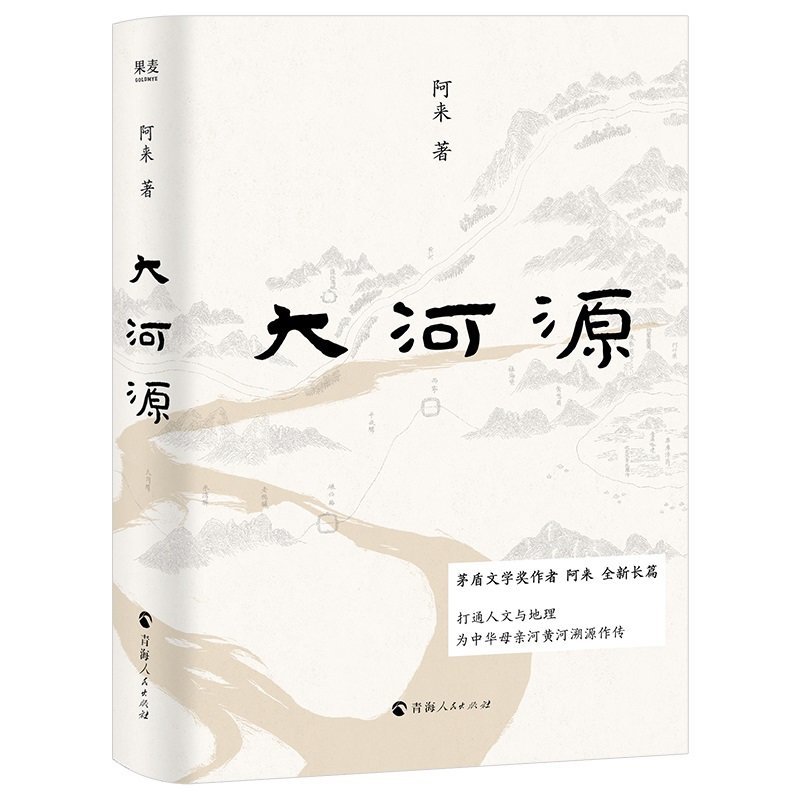
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在文学的长河中,著名作家阿来始终是一位独特的探索者。2025年3月,阿来最新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由果麦文化联合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这部作品以黄河源为书写对象,用诗性的语言、科学的视角,不仅展现了黄河源区的自然景观、地质变迁,更深入探究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记忆,是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之作。
同月,阿来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从李敬泽、郭义强、孟繁华、白烨、张清华、徐剑、徐则臣等近二十位著名评论家、作家的观点中,能深切感受到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厚价值与独特魅力。
从三江源到黄河源
阿来创作《大河源》,源于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约,最初他计划撰写一部三江源传。然而,实地考察后,他发现三江源在地理和人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长江源、澜沧江源相对封闭单一;而黄河源区则多民族融通、杂居共居,文化丰富多样。经过深思熟虑,阿来决定先为黄河源立传。
黄河源的认定在1974年或1975年由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确定,约古宗列曲是目前公认的源头之一。但实际上,黄河源头呈树状结构,有多条源流,且受水流侵蚀等因素影响,河源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长江源亦是如此。阿来在书中对黄河源的复杂结构和动态变化进行了细致描绘,让读者对黄河源有了更科学、全面的认识。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黄河源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却鲜少被书写,阿来的这部作品具有开创性。它不仅是地理探索,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底层结构的挖掘,体现了文明与自然的紧密联系。阿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写作,为处理与世界的复杂主体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科学与文学的交融之美
在创作过程中,阿来巧妙地将植物学、地质学等科学知识与文学情感相融合。他深知传统人文书写对自然认知的不足,借助达尔文的进化论、林奈的植物分类系统以及洪堡的地理学理论,为作品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他对黄河接纳第一条溪流场景的描写,将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诗意完美结合。读者既能从中了解地理知识,又能感受到文字的魅力,使黄河源的故事更加丰富、立体。这种融合并非易事,阿来凭借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文学才华,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黄河源世界。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评价阿来的《大河源》是“一部黄河源的百科全书”,具有深度和难度,展现了阿来的知识修养、思想、眼界和文字能力。作品以黄河源为中心,跨越时空,涵盖多方面内容,用小说笔法强化文学性,融合神话与科学知识,使作品更具深度和力量。
民族与文化的深度探寻
《大河源》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民族融合、文化发展的深刻记录。黄河源地区作为中国民族和文明的发源地,见证了多民族的生存、发展与繁衍。阿来在书中通过描写黄河由多条溪流汇聚而成的过程,隐喻了民族融合的力量。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相互包容、团结协作,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与黄河汇聚众流而成其大的特点相呼应。
阿来还对不同文化身份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文化是不断流变的,面对大自然,人类应关注基本问题,超越狭隘的文化身份观念,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世界,尊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指出,阿来写出了自然与人文相互交织的黄河源,物质与精神相互交融的黄河水。他通过黄河的贯通性和向上侵蚀等现象,隐喻了原始文明,展现了黄河作为母亲河对中华大地的哺育和对中华文明的隐喻。同时,阿来描绘了历史与地理双重演进中的黄河上游风貌,凸显了地缘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展现了民族融合、文明融会的重要地带。
与自然平等对话的文学表达
阿来在作品中始终秉持众生平等的理念,敬畏自然,尊重每一个生命,包括看似没有生命的石头、山峰等。这种平等观源于他行走黄河源时对自然伟大和人类渺小的深刻体会。在创作时,他摒弃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平等视角看待和书写所遇到的万事万物。
在描写植物时,阿来会深入探究其生长习性、进化历程,将植物视为与人类一样有生命历程的存在。比如,他对高原上那些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的植物的刻画,让读者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不屈。这种写作方式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然、尊重生命,也让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深度和感染力,引导人们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阿来的《大河源》具有生态思想的启蒙意义,连接了自然、历史、民族、文明等维度,纠正了人们对自然的误解,启发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阿来以专业精神填补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领域的空白,他的作品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
迎来生态保护的新契机
在黄河源的旅行中,阿来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科技为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积极影响。黄河上游的梯级开发水电站,不仅实现了发电功能,还能调节水量,有效减少了黄河下游的水灾。同时,水电站的建设为三文鱼等冷水鱼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使得原本生长在北美、欧洲高寒地带的三文鱼,如今能在黄河水库中养殖,成为当地的特色鱼类。
此外,太阳能板的铺设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态变化。在原本的半戈壁滩上,大面积铺设的太阳能板遮挡了阳光,减少了水分蒸发,使得地面开始长草。当地百姓利用这一变化,在光伏板下放养“光伏羊”,既解决了电站割草的难题,又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阿来坦言,这些现象展示了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为生态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也让人们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作家徐剑在研讨会上分享了阿来在考察过程中的故事,他提到阿来对植物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深入观察。阿来对青藏高原的植物了如指掌,从2009年开始就背着相机拍摄各种植物,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和专注,使他能够发现科技与自然之间的微妙联系,并将这些观察融入到作品中。
旅行的深度意义就是自我成长
阿来认为,旅行不应该只是浮光掠影的观光打卡,而应该是与大自然的深度连接,是建构更丰富自我、获得生命提振的过程。他强调旅行前做功课的重要性,不能仅仅依赖小红书等平台的简单介绍,而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他自己在前往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地旅行前,会先阅读相关书籍,了解当地文化,这样在旅行中才能有更多的发现和感悟。
在旅行过程中,阿来注重与当地的人、物、事进行深度交融和体悟。他批评那种过于功利和任务式的旅行方式,认为这样无法真正领略旅行的意义。他希望人们能够像他一样,在旅行中放慢脚步,用心去感受自然和人文的魅力,从而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获得生命的成长和启发。这种旅行观念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即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功利,而是注重内心的体验和精神的富足。
《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评价阿来的作品时提到,阿来通过实地勘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着丰富的细节,并且能够用文学将各种故事、各种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的作品背后有一种精神性的呼应和支撑,有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宇宙观。这与阿来独特的旅行方式和对旅行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他在旅行中不断积累素材,丰富自己的思想,从而创作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
文学创作需要不断超越自我
完成《大河源》后,阿来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计划下个月去追寻苏东坡最后一年的生命历程。苏东坡从儋州出发,最终在常州逝世,阿来希望通过行走苏东坡走过的路,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文学和人生。这一计划体现了阿来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对自我的不断挑战。
阿来表示,他对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也在考虑是否创作关于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的作品。尽管目前尚未确定,但他坚信,那些行走过的地方早已深深渗透到他的生命里,这些经历必然会在未来的创作中以某种独特的形式呈现。他始终秉持着不断超越自己的信念,渴望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开拓新的领域,为读者带来更多富有深度和内涵的作品,持续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书写自然与人类的动人故事。
在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对阿来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大家认为,阿来的创作不仅仅是个人的表达,更是为当代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扎实的写作,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关系。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强调阿来作品的文学价值,称赞他在《大河源》中展现出的宏阔视野与细腻描写、从容叙事、真情讲述、丰富内容和深刻思考。他认为阿来的这部作品是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载体,充分展现了自然、历史、现实以及生态保护的丰富内涵。
【访谈】
与黄河源灵魂对话,用文字为源区立传
近日,围绕新书《大河源》,记者对阿来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专访。谈及《大河源》的创作,阿来眼中满是对那片土地的深情。他缓缓道来,在黄河源的山川湖海间,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土地上,每一次观察都融入了对生命、自然、文明的深刻思考。
记者:《大河源》的创作灵感和过程是怎样的?
阿来:三年前,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请我去走三江源区,本来是打算写一部三江源传。2022年启程,先走通天河,去澜沧江,再上黄河源,两段合起来,把黄河上游李家峡以上段基本走完了。2023年6月我又出发,去了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等到动笔的时候,我觉得把三江源合写成一本书有困难,因为实地考察后发现黄河源区的人文多样性很突出,长江与澜沧江源区则相对封闭单一。所以我就决定只为黄河源立传,这个想法都没和出版社提前商量。从2022-2023年,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对黄河源的考察和创作。
记者:这次探寻黄河源的旅程,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阿来:这趟旅程很不容易,走了三次才走完。我们走的很多地方,外面的人都没有去过。真正要去的地方,到流石滩过后就离开道路了,鞋面被碎石迅速划得很旧,一双鞋才穿了两个月就看起来很破旧,但这正是它合脚好用的时候。
记者:当真正抵达黄河源时,会与您之前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阿来:以前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比较单一,真正去溯源才发现,黄河源头是一个树状结构,有很多源流,而且河源还会因为水流侵蚀这些因素不断变化,远比想象中复杂。
记者:《大河源》中能看到很多您亲自拍摄的植物照片,感觉已经从一种爱好变成了专业。您觉得呢?
阿来:书里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拍照的时候就想着把看到的那些独特的自然生命和景观记录下来,有时候为了拍一种植物,得在一个地方等很久,就为了捕捉它最美的状态。拍了二十多年了,应该说这是我用镜头补课的方式。过去中国文人写花鸟总爱托物言志,却连荷花生物学特性都说不清。如今得用林奈分类法,放进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树状结构里才算科学认知。
记者:您从30岁在黄河上游漫游到现在创作《大河源》,这期间您的创作理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阿来:30岁的时候,我漫游黄河上游主要是凭着一腔热爱,对文学和自然的关联感受比较直观。现在创作《大河源》,除了热爱,我还多了系统性的认知方法。我会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自然,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以前可能更注重情感表达,现在则更追求全面、深入地展现自然和人类的关系,通过作品引发读者对自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
记者:所以,您在《大河源》中运用了大量科学知识,这与您以往的文学创作有何不同?这种跨学科的写作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阿来:在传统文化里,我们对自然认知这块比较薄弱。而我在行走自然的过程中,越发觉得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去认识世界。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林奈的植物分类系统,还有洪堡的地理学理论。我在创作《大河源》时,就想把这些科学知识融入文学创作中。以前的文学创作可能更侧重于情感、人文方面,这次我希望从综合的角度,把人文和自然打通,更全面地展现黄河源,所以就形成了这种跨学科的写作方式。
记者:您在《大河源》中,对黄河源的生态环境描写细致入微,您认为当前黄河源生态保护面临哪些挑战?
阿来:黄河源生态环境脆弱,面临着气候变化、过度放牧、水土流失等挑战。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加速,影响河流水量和生态平衡;过度放牧破坏了草原植被,加剧了土地沙化;一些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记者:那么,《大河源》的出版,是不是可以在生态保护方面能发挥一些作用?
阿来:我希望是。文学可以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态保护的意识。通过生动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黄河源等自然生态的美丽与脆弱,从而激发他们保护自然的责任感。文学作品还可以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促使大家反思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记者:这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真正的生态文学?您如何看待生态文学创作?
阿来:其实,不管是生态文学的书写还是对其他文学主题的书写,我们都应该在人文之外,加入科学的眼光,用科学的观察、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比如,在若尔盖湿地,每株草都在完成亿万年进化史诗。作家不能只会抒情,得先搞懂这里的水文地质——为什么湿地蓄水近百亿立方米?为什么丰水季节黄河径流量在此增加29%?这些知识性书写才是根基。
记者:一路走下来,溯源黄河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来:探寻黄河源,不只是找地理上的源头,更是对生命起源、文明起源、民族起源的探寻。黄河源区的人文多样性比其他两江丰富得多,黄河上游的支流和主流上,好多民族杂居在一起,发展出了独特的灌溉农业和丰富文化。为黄河源立传,地理方面的自然变迁要写,民族互动、文化演进更是重点,地理和人文相互映衬,才是真正的黄河源传。
记者:您希望读者从《大河源》这本书中收获些什么?
阿来:我就希望读者读了这本书,能更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更真切地感受生命的美好。认识土地不是为了征服,而是要明白我们是如何被自然选择的。当真正了解每株草木的进化过程,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懂得生活的力量,也能懂得与万物共生的智慧,对生命和自然多一份敬畏和尊重。
记者:未来会创作关于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的作品吗?完成《三江源传》的书写?
阿来:长江源和澜沧江源在地理风貌、生态环境和人文特色上与黄河源有差异。等人文材料掌握更多,或者再次或多次亲身游历,有更多观察、更深体验,再来为长江源和澜沧江源立传。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