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孙贻荪是新中国成立后崛起的第一代诗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诗集似乎被人忘记了,但“陕西省略阳县文学艺术大事记”里却记载得很清楚:“1953年至1956年前后,铁路筑路人孙贻荪在略阳以亲身感受,创作诗歌,歌颂修建宝成铁路出现的新人新事,有《高山哪里去了》《姑娘们的心愿》《给略阳》等篇,后收入诗集《尖兵》,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是孙贻荪离别二野军大参与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转战又一个建设工地——宝成铁路的岁月。他一鼓作气,又出版了诗集《高原战鼓》,成为当时铁道上远近闻名的诗人。
这些往事,孙贻荪从不与后辈提及。被问急了,他就淡淡地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话就岔开了。那时,他在偏僻的自贡工务段工作。记得30年前,我还是一个文青,怎知天高地厚啊!贻荪师用他江苏话加四川方言的口音,对我开导加鼓励。那时的年轻人,一脑子的现代派存在主义尼采意象派立体主义,哪里听得进呢?我因为编印诗报受到打击,贻荪师仗义执言,让我心生好感。彼此交往一多,且30多年不断,于我半生是一个奇迹。
我想,这一“忘年交”能够维系至今,恰在于二者。其一,贻荪者,贻人香草,手留芬芳,这是他的仁者情怀;其二,在于他不轻易有求于人,这更凸显出他的赤子本色。我执编报纸、杂志20多年了,当然也编发、推荐过他的一些文章,反响尚好。
回忆起1996年,我决定为残疾人赖雨出版她的第一本专著《群山之上》,需要一篇反映赖雨人生踪迹的报告文学,贻荪师乐于承担这不讨文坛叫好也不赚钱的事务。年逾七旬的他,奔波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数万字稿件。20载倏忽而过,时至今天,这同样是关于赖雨最扎实的一篇传记。
贻荪师的写作道路就像他倾情一生的铁道,一根轨道为诗歌,一根轨道是散文,他是呼啸而来的一列绿皮火车,满载那个时代的梦想、光荣、沉重与忧伤。恍记得是1990年前后,他赠我他的散文集《风雨人生路》,是新时期以来自贡市的第一部个人散文集。1995年,他出版了第二部散文集《回望岁月》。两书都不厚,但他那种“正写”的散文言路,我至今难以消泯。
贻荪师买书读书不辍,这一习惯在老作家里罕有;但他并不守旧,也不会跟在新潮流后一味标新立异。他笔下的散文,既不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体忧患意识的仿袭,也不是拉美作家的函授作业,更不是跟着梅特林克一路狂奔的内陷、冥想式写作。他的散文具有帕乌斯托夫斯基、普利什文那种诗意加描述的典型美学特征,即在写景状物之余,渐次展开对人与事的追忆、感怀、思索。他的作品叙事性不是特别明显,也没有向非虚构写作竭力靠拢。我发现,是抒情性而非抒情式的写作,构成了孙贻荪文学的压舱石。这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对遍布于铁路两侧的劳作生涯、抗美援朝以及对平凡岁月的挖掘、反刍与缅怀,这不妨看作他对早年诗写传统的散文化继承。大地上,铁路蜿蜒纵横,就像孙贻荪的掌纹。他的散文即掌纹的拓印,也构成了他生命的“大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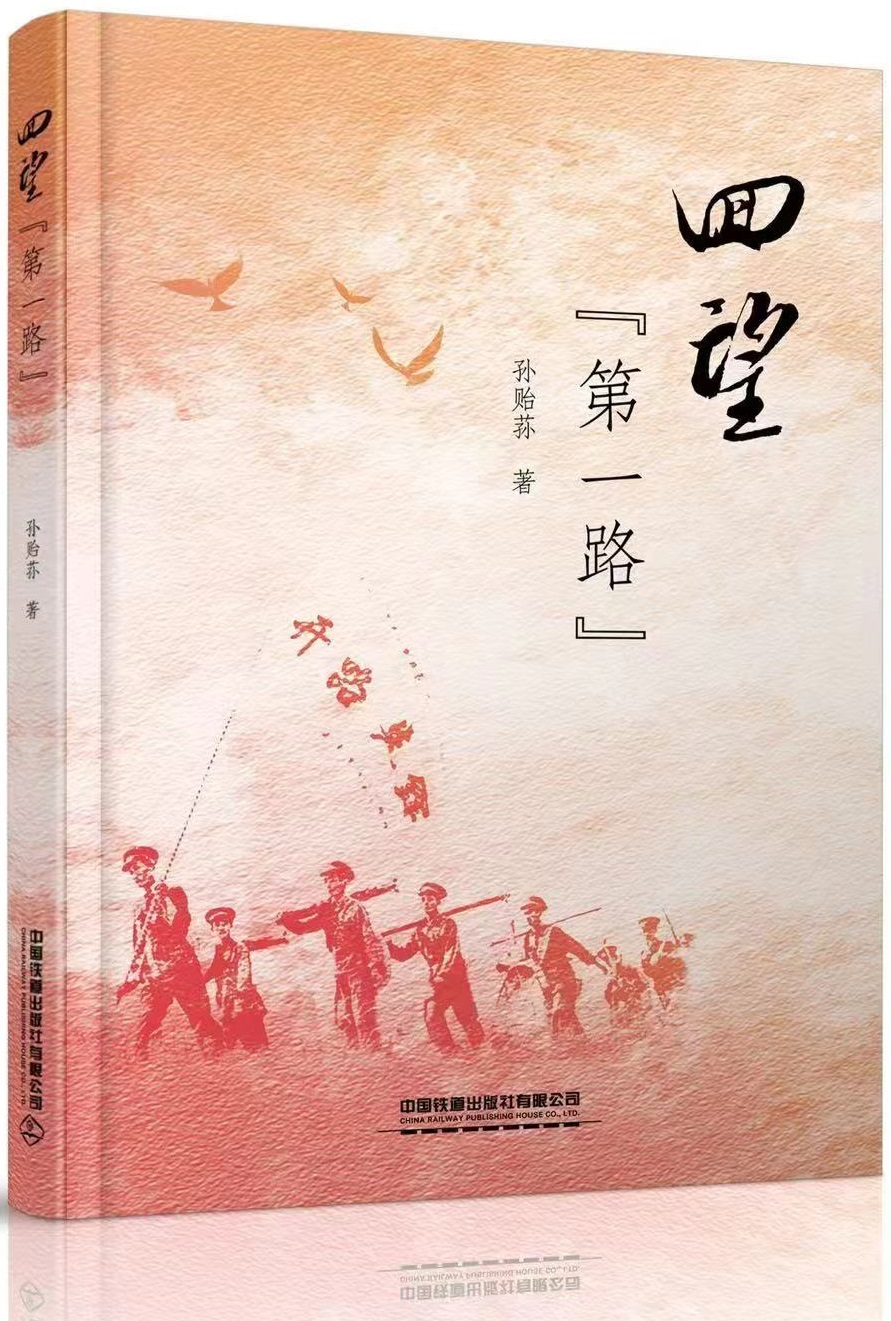
孙贻荪师《回望“第一路”》这部散文体的人生回忆录,着重描写了参加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与全程亲历成渝铁路的修筑过程,让我们回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火热年月,见证新中国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重温这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与重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孙贻荪用充满深情、充满细节、充满生活气息的笔触,描述了一个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物与事件。他们用热血与生命,构筑成一组时代的群像。借助于此,孙贻荪也完成了自我的文学造像。同时,书里也有不少“闲笔”,记录那个时代大众生活的诸多片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回忆录也是一部具有巴蜀风物价值的生活史。
孙贻荪师老老实实地写,他在激情、思辨与叙事之间徜徉,从没有刻意地“反抒情”“反叙事”,更没有标举什么“反价值”,渴望向天空突围。散文不能像诗那样高蹈而飞翔,散文的大地气质决定散文只能俯身大地,在消磨、耗散、委顿、机变、沉默中,抵达一座辉煌的、鼎沸的人居城池。他来了,他看见,他说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正写”。我近年在散文界提出“正写才是硬道理”,正是基于当下散文家过度仰仗修辞所造成的弱力、缺血、蹈虚、呻吟而为之。奇妙的恰在于,本来应该闭嘴、夹紧尾巴的南郭先生们,如今却声若洪钟地当起了文学师爷……散文不应该成为“南郭修辞术”宰制的地盘。我认为,孙贻荪散文彰显出的光亮、血性、通透、节制,恰是汉语散文的正脉,所谓“正写才是硬道理”,这也是汉语散文应该重视的一大向度。
记得贻荪师满80岁时,谢绝了宴请,悄悄出版了一册《别样人生》来“自我纪念”。翻看着他浓缩在书里的人生踪迹,不胜感慨。我与几位作家说过,这是一个多么快乐、多么可爱的老头儿!白云苍狗,蜀犬吠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睨眼看淡功名,热眼专注真情,成为《别样人生》最妥帖的注脚。
2016年初,春寒料峭时节,我在铁像寺水街的散花书屋举行《成都笔记》《蜀地笔记》分享会。贻荪师来了,不但买了一大堆书,还向不少人推荐我的作品。作为晚辈,我只能把他的鼓励当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临近散场举行宴会时,他却悄悄走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
在贻荪师的鲐背之年,呈现在大众面前的这部沉甸甸的回忆录,就是一部非虚构之书。与其说是他的“自寿”,不如说是他以毕生之力,献给铁路、献给时代的一个礼物。
也许,我们置身于一个瓦釜雷鸣的文学时代。我曾经为贻荪师八十寿辰写过一首诗《银杏花》,这其实是他留给我的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文学造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很多人都见过银杏,也见过它的果实白果,可却很少有人见过银杏花。银杏花与银杏,构成了诗中的种种隐喻——
这些高枝上的盐
委地而金黄
暮冬的蜀籁裹挟了江南雨烟
银杏花像卡夫卡的甲虫
在革命的中途
被一次意外掀翻
只用毛绒绒的脚凌空蹬踏
成为了汉语的花
花是被杜鹃的叫声震落的
簌簌而落是金蝉自救的招式
人们面对古钟
可能想起父辈
也可能想到黄铜的安宁
花粉在钟声里飘开
高挂迎亲的灯笼
成就了成都平原最灿烂的子夜
(《回望第一路》,孙贻荪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24年11月)
作者简介
蒋蓝,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