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林
阿来为黄河立传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大河源》,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溯源,更是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深刻叩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原典中讨论的“诗”(Poiesis),本意并非特指诗歌文体,而是指广义的创造性模仿艺术。这种理论基因决定了文类包容性。阿来的《大河源》用散文的经纬,编织出一张立体的生命之网,在生态书写、文化寻根与叙事重构的三重维度上,构建起独特的三重生命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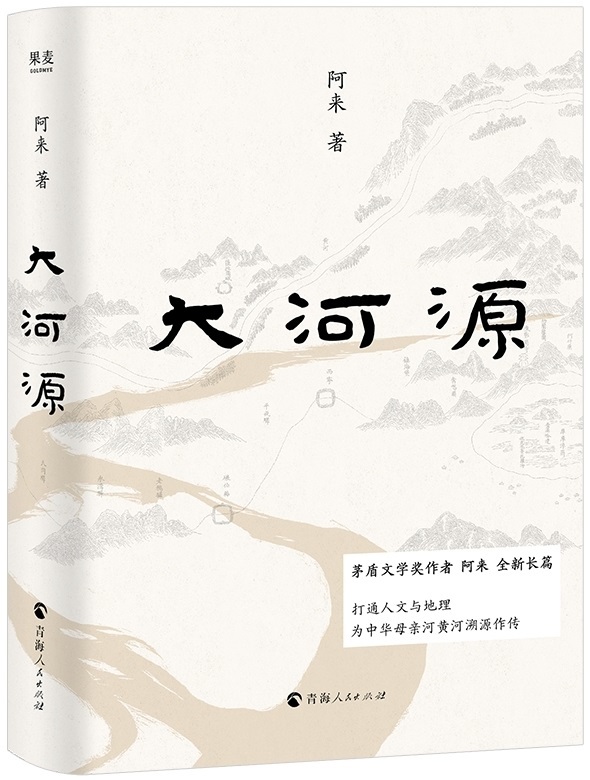
辩证维度的生态诗学
在阿来的笔下,耸起的丘岗因风雨冰雪的剥蚀变得平坦浑圆,伫立天高地阔的黄河源头,总对自己不知身在哪个坐标感到茫然。一只普氏原羚的生产,小羊的半个身子卡在母亲的身躯;一只羊被狼袭击,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高原的生态危机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图景,这种生态书写超越了简单的环保呼吁,在野驴与越野车的相遇中,现代性对高原生态系统的入侵,暴露出文明本身的悖论。
扎陵源的自然演进被人类活动反转,数万年形成的草场正在退化,植被减少,黑土裸露,风雨剥蚀,重回荒漠。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玛多县地域辽阔、牲畜众多,在全国是很富裕的,人均收入两万多元。但后来气候变迁,草原退化,由富转贫,让人不胜唏嘘。
站在生态危机的深渊边缘,细碎的沙粒留下长长的弧线,灰色云雾把天空和水面混同一体。牧羊人对藏野驴的目光没有惊喜,却是忧伤与迷茫,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的矛盾令人无解。野马滩的野马被猎杀,成了无马滩。从古至今,人类基因潜伏的狩猎原始冲动和生态保护成为悖论。
阿来渴望,文成公主一路西去、向着黄河源头的琴声里,“一定有湖水的激荡,有流云的飘飞。”面对窘境,作家掘出了希望的种子:一只人造建筑上的鹰巢,巢中两只见人并不惊惶的雏鹰,无意中成为人与自然关系重建与改善的见证;塔拉滩上的光伏板矩阵与羊群,呈现出的绿色回归,表达出荒漠生态改善的科学路径。
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也是所有生命共生共荣的世界。由此揭示生态书写的终极启示:造物劈凿,种群生息,诗人描绘,历史作注,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网络中的普通节点。
镜像寻根的文化诗学
文化身份具象化为无数镜像,既非对传统的亵渎,也非对现代的臣服,而是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大河源》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河,在文明长河的碰撞中一路前行。
深情而富有特色的文字,流淌在黄河之源。在第一回“黄河源上玛多”,鄂陵湖的蓝映照天空的色彩,“隔着浩渺烟波,隐约可见南边一抹黛青色的山脉蜿蜒,那就是著名的巴颜喀拉山山脉。”湖口溢出的黄河水,一路接纳高寒草甸与沼泽的溪流,曲折奔流。看到岩画,作家仿佛看到那个手握石器的人,在山顶,毛发飘拂,黝黑的面孔浮现出神秘的笑容,视线从低空转向地面,内心的启悟心醉神迷。
写七朵花开的欧氏马先蒿,“如果用草原上的物产作比,那是一罐牛奶面上凝结的酥油颜色。花朵们似乎在用这种润泽的色彩悄声细语。”并且写道,每朵花都像头顶紫黑的小鸟,试图歌唱。动静瞬间,作家虽然听不懂歌唱的语言,但外化的情感、内在的观念,已在黄河源悄然而至。
玛多县城的渡口叫玛查理,这是藏语与蒙古语复合的地名词。作家解释,“玛”是藏语,本意是孔雀,喻指黄河。“查理”是蒙古语,意思是河沿。两种语言叠加,意思就是黄河沿。面对唐蕃古道遗迹,作家详述唐朝与吐蕃时战时和的人文历史,两国交往的恩怨情仇在古道弥漫。《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黄河浮桥,使贵德成为沟通边地与中原的文化纽带。
类似这样的地理人文回响,在黄河源不断涌现。征途漫漫,往事历历,厚重的人文历史伴随作家开始下一段文化寻根。这种人文历史与地理的混血状态催生出新的表达维度,每种转换都是一次文化的转译,新的文化主体向阳而生。
叙事重构的时空诗学
散文的叙事结构在文本中交织成多维的时间网络。在牛头碑园,史前人类留下的石刻勾勒出动物的形象。作家写道:“那都是一种蒙昧的觉醒,都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空间的宽广,到时间的久远,动物的身躯被太阳和月亮辉耀,眼睛汇聚浩瀚天宇中所有星辰的光芒,试图探索人类最初的审美表达。
湖水的岩石显示出久远的时间纹理,曾经的远古大洋,而今高耸成岸,风来化解,雨水剥蚀,分解为铁灰色的沙。文成公主,翻日月山,过青海湖,千里迢迢,来到鄂陵湖畔的迎亲滩。历史的风云与美丽的故事交汇,这种时空折叠的叙事策略,打破了现代性单一时间观的藩篱,让过去、现在、未来在叙事场域中平等对话。
多元感知的交响制造出惊人的美学效果。在九曲黄河之地,阿来脚踏古道,心头想起遥远的历史。来到旷野高处,见低垂的灰云被太阳镶上金边,消失的扎陵湖重现眼前,辉映蓝蓝的天空。敦煌藏经洞的《白云歌》款款而来:“遥望白云出海湾,完成万状须臾间。忽散鸟飞趁不及,唯只清风随往还。”
这种视角碰撞形成认知维度的新拓展。黄河,我们面目模糊的母亲,在阿来的笔下,再次看到她青春甚至年少的模样。在叙事时空的裂变中,新的认知范式悄然生长,而叙事最终给出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两种坐标系的叠加态中,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生存智慧。
在大河源深处,阿来埋藏着一面照见文明本质的棱镜。《大河源》的终极追问,不在于如何保护高原生态,也不在于怎样传承文化,而是试图回答:在技术文明重塑一切的今天,人类该如何重构与自然、与传统、与自我的关系。
与通天河,再见;与巴颜喀拉山,再见;与黄河源,再见!但是,“还有很多山在前面,还有许多水,奔流在群山中间。”当作品的最后一行文字消逝在雪原尽头,这个追问仍如高原的风,持续叩击着每个现代人的灵魂。或许答案就藏在三江并流的壮阔里——不同的生命之河终将在某个纬度找到共生的入海口,拥抱生命之美。
(《大河源》,阿来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
作者简介
张洪林,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文史工作。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