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诗集为什么叫《新成都诗歌》?首先,它不是刻意标“新”,也不是要强调和“旧”的对立和抗衡,更不是要别出心裁地拓一条当代诗在地吟咏的“新”路径。我的理解,这是龚学敏将自己置放于一个“新成都人”的特殊视角,在成都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以及叠加了信息时代的崭“新”阶段下,对非主流叙事之外的新的吟咏主题的垂注和关切。这种取“新”思维,看上去充满诗人个体经历的偶然性,其实也喻示着新诗在地吟咏的某种必然性。汉唐以降,宋诗长于说理,明诗习于雅容,而清诗则矜于气节。从时代需要出发,当代成都的诗歌吟咏,太需要这种拓新精神和新拓主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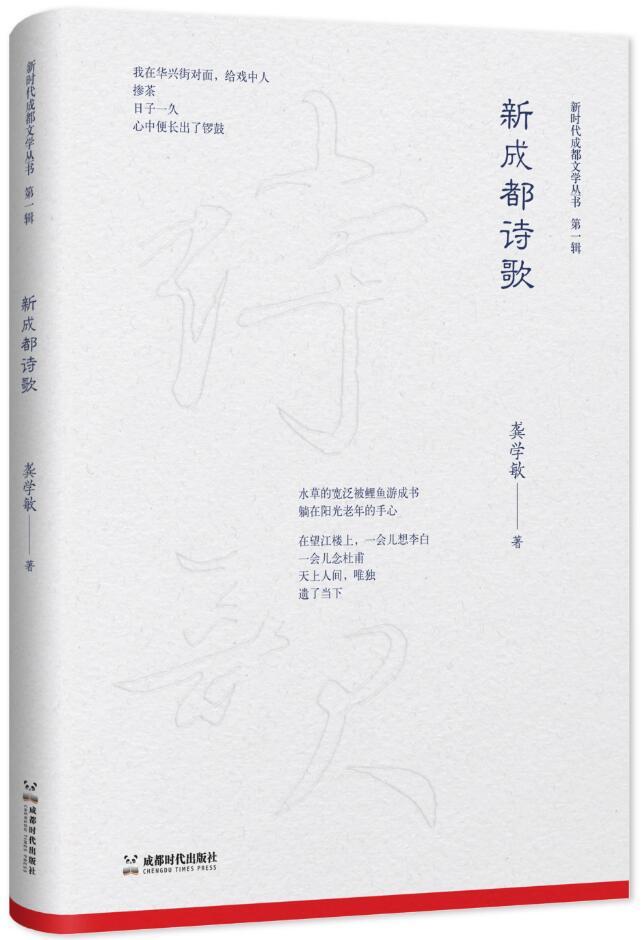
具体而言,全书74首诗,接近三分之一在写成都明确的地理标志,另外接近一半在写成都的名物,还有两部分分别写成都的人和事件。它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即有意无意地跳开某种主流的命题,而趋向极目和动心的某个非主流瞬间。
如成都地理标志,我们几乎看不到合江亭、青羊宫和丹景阁、东安湖这些似乎新旧都不能抛弃的代言,反而对悦来茶馆、莫舍咖啡、惜字宫街、文殊院坝坝茶这些比较文艺的地理标志生发出强烈的兴趣。大约越市井的地方,便越存在稍纵一逝但却惊才绝艳的诗性启发。而那些主流代言,或许反复激荡的都是平庸的陈词滥调。
再比如,关于成都的名物,诗人的兴致,似乎也不太垂注于太阳神鸟、大熊猫、锦绣这些看上去厚重而高级的名物,而是偏爱白鹭、产房、邮筒、药铺、夜行火车、女贞、麻羊以及空地上的鸽子、围墙上的流浪猫。这些或许是这城市的边角,但也可能是“最昂贵的补丁”,接近于奢侈品设计理念上的返璞归真。注意到诗人惯常用“补丁”这个词的实际,我认为这或许就是“新成都诗歌”从时代需要出发,对汉唐以降的成都在地吟咏打的一个补丁。
另外一重新,来自于诗人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诗人似乎也摒弃了宏大叙事,热衷于进入夜钓者、僧人等凡人的一小部分打开的世界和看川剧、遇到成为粮食的雾等等,喻示着某种可能的偶然遭际。这些人物和事件,第一次系统化地以当代诗的名义,向更多涌入成都的新人,包括生长于斯的“老人”,提供了全新阐释成都这个城市的诗意入口,从而协助小说、配合散文、联手报告文学以及一切文艺载体,为拓宽新成都的人文意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诗意视角。
也不是没有旧,但诗人却是在用旧的主题,来装新的内容,更是在刷新我们对旧的刻板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旧为新”,或者旧瓶新酒。比如写锦江,写望江楼,念想李杜之外,天上人间,唯独遗了当下——当下即新,永不过时;比如写九眼桥,“一群鳝鱼从桥孔送亲,一群鳝鱼从桥孔迎亲”,岂止一个新,简直就是奇幻;再比如,写青城山,“想得道的人太多,失德的身影更多”。得道的人和失德的身影,从实景到虚像,时代的崭新批判不是减弱,而是增强。
新诗存在的时代意义是什么?是诗人心中随时需要敲起的时代锣鼓,而不是屈膝躬身,向历史的圣像下跪。如此,当我们注意到“锣鼓”这一事物及其隐喻在《新成都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事实时,我们就会隐约捕捉到这些看上去平凡的成都物色和市井人物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意象,以及诗人借诗歌言情说理的本意。肤浅或者深刻,疑问或者感叹,接受这样的新成都,或者吟咏这样的诗歌,无论对时代还是对读者个体而言,都将收获和吟咏“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等古典诗歌不一样的体验。
(《新成都诗歌》,龚学敏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7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