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暗夜里,我听到自已的呼吸。我知道,我并不强大。我的生命就存续在这一进一出的呼吸之间。生命如此奇妙,它让我们吃尽苦头,又让我们深感幸福。我们无法延长青春,也不可能永生,于是我们需要尽力去做我们深爱的每一件事,这过程使我们的力量和勇气得到增长。那些不曾远去的美好,热泪盈眶的瞬间,难以忘记的日子,我们当以我们喜欢的方式存留。”这是作家阿呷在散文集《就这样开始》里“自序”的一段话,也是一名资深出版人走出编辑地域的一个转身,一次拔足狂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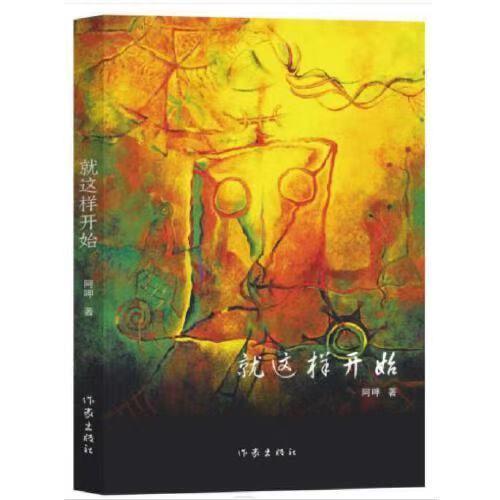
6篇均是逾万字的长文,水、神鸟、九寨沟、成都记忆、父亲与我、故乡,刊发在《人民文学》《青年作家》,看似无逻辑,其实暗藏着作者生命中的某种命定,更透露出她与散文叙事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
在我看来,阿呷的散文,具有一种善跑者的肺活量。她不紧不慢,将自己过往的生活与经历,用密不透风的细节予以存留和呈现,不是“将往事留在风中”,而是这些被标的为路标与树号的往事,不但是自己经历过的证词,而且它们一直活在人的血脉深处,还在向着未来伸延根须。当这些根须举起露珠以及露珠里的阳光之际,更昭示了作者的方向。
在《九寨沟》一文中,在这些景致背后,蕴含着滚滚不绝的爱与善:“静如镜面的湖面,没有一丝波纹,半山美丽的秋色整个地倒映在蓝色的湖面上,清晰如镜,让人分不清虚实。远处两座山的夹缝之间,松柏成林,彩林在对面近湖的山坡上夹杂着生长。我第一次看到明黄色的枫树,它的叶片顶着光……它们枝叶婆娑,在靠近湖边的上方成片地生长。周围是一些深深浅浅偏橘调的黄叶,然后,隔着一小片常青的林木,猛然地,又是一圈一圈密密杂生着的红叶。姿态好看的灌木和挺直的乔木交错而生。此刻,太阳已经隐没到一座山的后面去了,但它的余晖仍旧长久地停留在山上的彩林之间。湖水暗下来,光已经到了山坡上。我们一行人就地坐在海子边上,大家都没有说话。”
读到这样干净、细致,将审美观压缩到山水深处的段落,我不禁想起了梭罗,想起了契诃夫,想起了普利什文,想起了阿斯塔菲耶夫,个中不但有生命的礼赞,也有面对大美而不敢言说的暗自神伤。正是这样的克制状态,阿呷的文字才具有独特的文体意识与“事随文字而游走”的雅洁情致。
我还注意到,在6篇文章里,不时有作者的哲思段落异峰突起。这是阿呷的随想录,也是阿呷的生命断片。从这些自然而然从叙事里升跃而起的哲思中,我读到一个人从经历提炼经验、再从经验提纯智慧的缓慢过程。生命的确是缓慢的,一当我们与“比缓慢更缓慢”的事态相遇,更应目睹到事物的纤维与树叶纹理,就可以选定其中的一片,那才是属于你的贝叶!
我曾经说,四川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散文家,以阿薇木依萝、雍措、南泽仁、韩玲、黄薇、杨庆珍、熊芙蓉、刘馨忆等为代表,相较于峭拔的四川小说与诗歌,将四川散文从历史性的凹陷之地拉回到正常状态,注入了异彩。阿呷的散文集《就这样开始》,进一步佐证了我的上述判断。
鉴于阿呷的凌空出现,也可以这样认为,她是一位散文的闯入者。法国学者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同体》指出:“闯入者凭强力进入,让人惊讶,或诡计多端。无论哪种闯入,都是没有权利、没有事先征得同意的进入。在陌生人身上必定有某种闯入的东西,否则陌生人就失去了陌生性。如果他已经有进入和拘留的权利,如果他是我们所等候的,是为我们所接受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人意,不受欢迎的,那么,他不再是闯入者,也不再是陌生人了。”其实,闯入者就是创新者,这也是历史上公认的“闯入者”这个词的美妙定义。
写作就是照亮自己的大光。阿呷这样总结过自己的写作:“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是否会阅读或者书写,我们终将回到文学的怀抱,不是吗?一些刻骨铭心的温暖,似曾相识的场景,它们是我们记忆中永恒的诗篇,一直都在,带着光亮,直到生命的尽头。”
(《就这样开始》,阿呷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