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仕江
退休教师龚昫西新书《涉笔犁痕》即将面世。这是一部散文随笔集,是他从蜀南进入成都后写下的篇章,经过10多年累积成册。有的文章,我在早年陆续看过,对他曾经生活劳作和教书育人的那片土地,并不陌生。尤其是他书中写到的军旅时光,也曾与我最初军旅的地方,同在印度洋之上雅鲁藏布江支流的尼洋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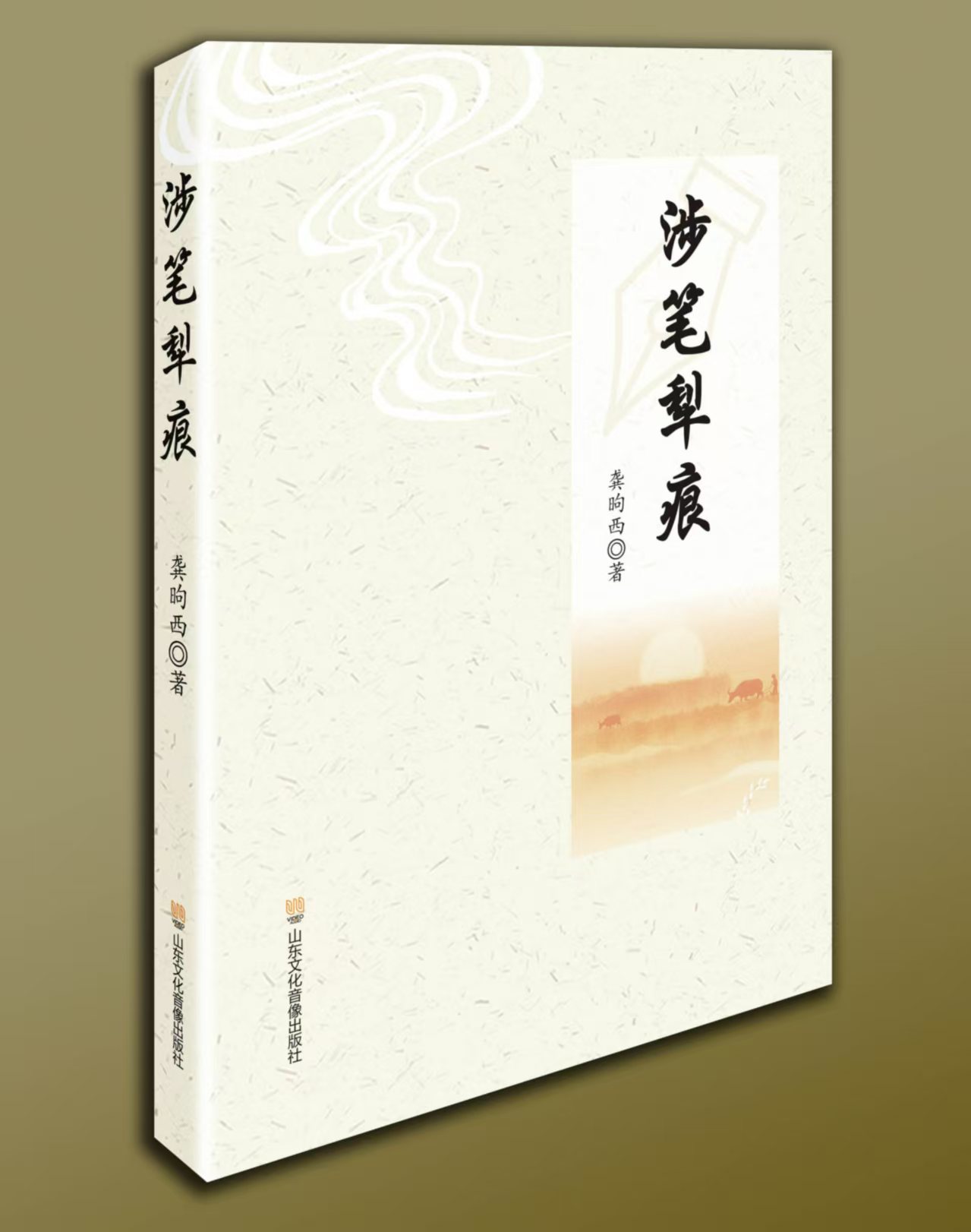
尽管我们的人生代际有时代差异,但细读书中的篇章,不难发现,龚昫西心里早就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但年轻时苦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压得他不敢有多余的文学细胞去滋生未来梦想。尽管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作文,每次都得到老师的表扬,并且在不同的班级传阅,可是贫寒的家庭使得他连一个作业本也买不起,欠交学费也是常事。他只有拼命地参加劳动,替家里挣工分才是缓解燃眉之急的大事。
所幸的是,龚昫西通过当兵这条路,暂时脱离了蜀南丘陵一个名叫“章佳”的地方。
很多中外作家为什么写作的理由,总有人回答:为了离开故乡。在龚昫西笔下,故乡的底色,记忆透视出的多是生命的不堪重负,母亲在丘陵阴郁的天空下,“驮”着孩子们长大。如此画面,恰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白电影,亦仿若动物世界的斑羚飞渡。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散文母题创作中,书写母亲的太多太多。因为母亲之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太熟悉不过了,人人都以为这个生命中最熟悉的人很好写,并且人人都抱有自信,一定能写好自己的母亲。然而,我们读到千篇一律的伟大“母亲”太多太多。
龚昫西笔下的母亲,没有鸿篇巨制的构筑,也没有细腻动情的文采,更没有冷静深刻的内省。好就好在一个“驮”字,击退了命运看似“恶意”摆布的不公,用力地抓住了读者眼球,让人看见生活的姿态,掂量生存的重量,感叹命运的多舛。
有时,我们看球赛,常常会听到足球解说员批评某位球星,未能将那么好一个球踢进球门,而指责他的技术动作太过粗糙;甚至有时我们听CD或看演唱会,也会发现有些歌手的气息未能把一些精彩歌词,诠释处理得更加彻底、深入、内敛、走心。
相比之下,对于散文随笔所谓含金量的写作技术,这样的情形,在我看来则少了几分“静”气的修炼。“静”注定是蓄积力量后的一种准确表达,它可以让人听见力透纸背的声音。但龚昫西的散文随笔顾不了那么多技术讲究,因为他对时间的紧迫与警惕,有时表达在与人“无痕”聊天的叹息里。于是,他以笔为旗,用写作保持如此热爱生活的方式,便有了这些“有痕”的齿轮,纪念岁月不虚。
年过七旬的龚昫西不喜欢打牌、下棋,家中事务多为夫人包办,因此,他笔下的夫人,是这个世界“业务”最繁忙的人;他的儿女优秀,他们之间多数时候互不干扰,互为尊重,女儿总像家长一样呵护他晚年的理想追求,保障他专心致志地享受创作空间,并且奔走相告,助他圆梦。
他笔下的另一个“我”,经常处于乐观幽默状态。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状态不失为幸福人生的舒适时光。他手里端着茶杯,思考的事情却多是文学。他在成都念故乡的亲人朋友,也想念小城里那些曾经被他发现的文友;他讲起一同入伍的墨脱战友,有时会不顾时间冲突,打个电话给对方;之于那些洗手金盆不干文学的朋友,他谈起就深感遗憾,常笑自己多情地生出“怜惜”之情;有时,他甚至打着手电去茫茫人海找寻那“失约”已久的朋友;他的“热爱”带着浓浓的乡音与偏执,充满丘陵泥土里埋藏的红苕味;他笔下忆及的旧人或新事,宛如麻雀在桑树上啄过的桑泡(桑果),腐烂中惊现人与食物的本性。
因为有了丘陵乡间生活的殷实体验,龚昫西的散文随笔,琐碎中不失生命年轮的斑点和温度。泥土如波澜翻滚在阳光下的痕迹,像老牛在田野里涉过的诗行。这些诗行原本是故乡赋予异乡人审美的一种形态,但在龚昫西的文本叙事里,充满乡间的打趣,如豆腐是“灰妹(灰馍儿)”“吃盐巴不要(情)钱”,艰辛劳动后的豁达与解嘲,“钱”和“情”难分伯仲,他还原的多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人生老来最怕无聊,太多无聊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热爱。好在有一颗文学的种子,在步入人生的下半场后慢慢开花,这是热爱文学带给一个社会和家庭的好处,也是一个人在孤独中热爱的能力所致。保持热爱,无须极致,生命终可慢慢抵达不衰之境!
是为序。
(《涉笔犁痕》,龚昫西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24年12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