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新
1
与诗歌结缘于童年时期。记忆里,当年的小学语文老师风流倜傥,会玩花式篮球,爱唱情歌,爱声情并茂地诵读诗歌。他常常在课间与我们一群毛孩子厮混在一起,带着我们在简陋的教室里闲话古今、吟诗作赋。夏天,教学楼外的田野间吹来柔和的自然风,他便借着风势,取出几把印有佳人或才子的布制折叠扇,现场挥毫题诗。顺着扇子的骨架,从薄薄的扇面穿透过来,一眼看去,极为遒劲飘逸。
大概是受了语文老师的启发,有一天,我坐在教室的墙角,拿一截指头长短的粉笔,在掉漆的绿色墙体上写写画画。最后,一首古体“打油诗”出来——那是记忆中我最早诞生的一首诗。
高中毕业那会儿,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那时,至亲已相继离开人世。于是,手机的记事本里,便开始累积各种宣泄情绪的文字,形式似诗,好不伤感。那些时而如湖水般隐秘、时而似大海般汹涌的文字,与少年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动因大为不同。那些怀念,那些呼喊,那些撕心裂肺的痛,那些沉甸甸的情,无以传递,只能诉诸文字。
2
我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诗歌,则是近来的事了。这期间,经历了从“以我手写我心”,到阅读、启蒙、输出,再到批判式思考和自主式写作的过程。10余年间,我更多的写作集中在随笔、杂文和小说。这些形式的写作,相对于诗歌来说,带给我的体验,更近乎一种含蓄的表达。这与我“中庸”的个性有关。因为我知道,身处于生活的夹缝之中,“创作”于我,既是救赎,也是一种本不应被我抓住的“奢侈”。投入的情感浓度一旦过高,要么“羽化登仙”,要么万劫不复。
直至参加工作,属于个人的时间是碎片化的,而不论是眼前正在经历的复杂人事,还是青葱岁月中滚雪球式的迷惘、信念、执着、孤独、犹疑、困惑……五味杂陈的念想越积越多。终于有一天,到了喷薄而出的时候。于是,诗歌再次款款来到我的面前,向我敞开她的广阔世界。在生活的雷雨闪电还未完全将我击倒之前,诗歌成了一剂猛方,让我给心灵松绑,许灵魂喘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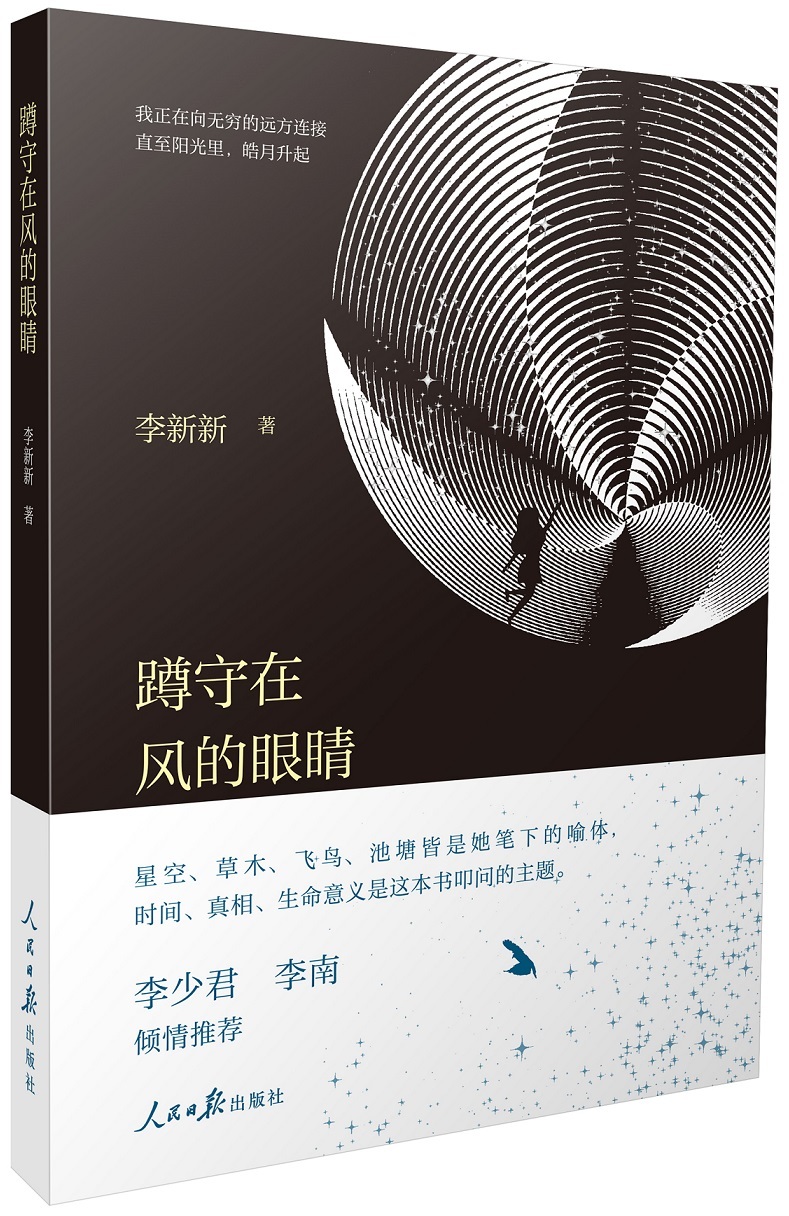
这本诗集中,近半数诗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着魔般徜徉在诗的海洋:走在四面围墙的院子里,拥挤在地铁上,在热火朝天的人群中埋头吃饭,在夜晚寂静的灯火下品咂孤影……在这些活动的间隙,诗意上头,几段诗速成。我知,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如胎儿般,在母亲的子宫里孕育了许久,直至某个月明之夜,一个新的生命终于诞生。
当心中那些交织如水、堆积如山的事物,通过文字的梳理和思想的萃取,在诗歌中排兵布阵,找到各自的归属,我忽觉内心渐渐敞亮,行走的脚步变得轻盈,头顶的乌云在风中散开,而注定高飞的风筝,正奔往它的天空。
3
最初,我之为诗,基于或苦涩或热腾腾的生活,基于生命本真的体验;后来,由“自发”到“自觉”,便有了进一步的自我凝视和向外的探求。但若离开本源性的冲动,我的诗歌创作将无从谈起。所以,在我的诗里,始终有一种原始的、自然的,甚至近乎野性的“因子”存在。我称之为“因子”,是因为实在难以将其具象化,它可能源于先天的生命底色,可能是后天的命运指涉。不管怎样,它们是我内在的一部分,已融入血脉,塑造了我如今的人格和秉性。
相较于我读过、见过的许多诗人,他们拿生命在写诗,在诗歌里倾注自己全部的爱,甚至将此生奉献给了诗。就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我无法与他们比肩,我不是将生活全部交付于诗的人。这于我不切实际,况且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顺利地攀登诗歌的高峰。但我的生活不能没有诗意。这是我与诗的关系。或者说,是我所理解的生活与诗的关系。诗歌带给我直接的诗意化的体验,让我尽可能以超然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繁芜之事;同时,在我充满挑战的30年的生命历程中,属于我的日常化的、生活中的“诗意”,并非全部来自诗歌。所谓“他乡遇故知”,别处亦风景。生活太苦的时候,稍稍有阳光照拂,便觉那就是糖——而这样的“糖”,可以有形亦可以无形,可以是一个眼神、一段曲子、一片落叶、一阵风。
由此,我常常想起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后来,海德格尔对此进行哲学式的解读。在我心里,“诗意地栖居”,不仅关乎诗歌,关乎文学,更关乎日常的琐碎与朴素的生活。
诗,不必在远方。诗意,更不是束之高阁的观赏品,它本身即一种生活,是对待苦难生活的态度。对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过的人而言,诗意是那一朵掐不灭的火光,在幽暗中闪烁,于绝境中开辟希望的小径。
4
当下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诗歌乃至文学,是一群远离生活之人的自娱自乐;写诗者不合时宜或耽溺于脱离实际的幻想;一遇到现实的难题,诗便沦为无用之物。总之,诗被当作一种“避世的梦幻”。从我的经验看,这种说法抨击的多是那些空洞无物或无病呻吟、玩弄语言和修辞的、故作深沉或附庸风雅的诗,而真正从灵魂深处淘洗出来的诗,是动人的,也充满了力量。它给人以净化、释放、反思和回归。
作为写诗者,我始终注视着这片土地,注视着土地上的人。除了自我的挖掘和审视之外,我在诗中所想要触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连接中的共性和个性。我试图跳出个体的经验,去窥视萦绕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情绪——这是一种时代性的情绪,被打上了个体的烙印;我试图去探索某种群体的困境,虽然很难找到一把开解的钥匙,但一旦发出追问,必将隐含我个人价值追求的一部分。我在诗里剖开自己,也解剖外事外物。我尽可能冷静地观察,但流诸笔端的文字,也许充满了激情,甚至直接呈现一种彷徨、一种诗性的“呐喊”、一种反讽式的沉思、一种深刻的绝望。但彷徨和绝望之后,是永远绝处“谋”生的执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依旧热爱生活”的旷达。这是我和诗之间达成的“共谋”,也是我想通过诗向己身之外的世界传递的信号。就像风中之“眼”那般,保持一种虔诚“蹲守”的姿态,一种身处疾风、狂风、暴风、清风、微风之中时“若等闲”的定力,一种怀揣理想、锚定目标的笃定。
5
写诗的过程,起初是一种燃烧。我在这本诗集中,燃烧了自己。我将一些隐秘、过往、沉痛,以及短暂而刻骨的时刻在诗中呈现,也将思考的碎片忠实地陈列。我所呈现的,便是精神所抵达之地——但也许还不够。诗,终究还是一门艺术,自有它独特的气息和纹理。真诚的书写自然重要,掌握通往“诗言诗语”的符码亦不容忽视。我无法确保自己倾吐出的每一首诗,同时在情趣、审美、智性、语言等方面臻于完美,我也不认为这种对“完美”的理解和迷恋,对于成就一首诗真有必要。在我看来,好的诗,犹如断臂的维纳斯——她的某种缺陷成就了她的艺术之境。
在诗中燃烧,我当然希望其迸发的火光能闪烁得久一点、释放的能量持续得久一点。但总有一天,诗人会迎来创作上的“灰烬”;而生活,也终将被火光渐灭之后的余烟填满。然而,对早已掌握诗意密码的人而言,文本意义上的诗虽然可能会消逝,作为精神追求的诗意不会远离。它从生命的沃土中诞生,也必将回归生命的本真。
(《蹲守在风的眼睛》,李新新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1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