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叶
人是经验的容器。在曹有云诗集《经验之花》中,“李白狂喜过的春天/杜甫感伤过的春天/……长安的春天,西安的春天/不亦同一个春天”“我们陷于名利幻海,不能自拔”,狂喜与感伤、功名与虚幻,仿佛桃花和雪花一样同在于春天,受到激励和煎熬的从来不仅是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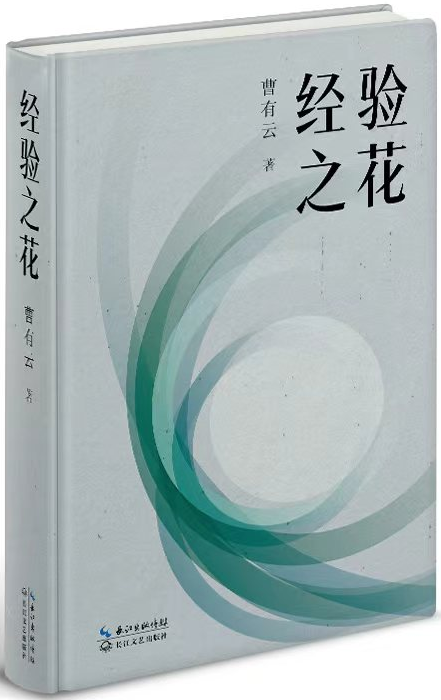
《经验之花》的扉页题写着里尔克的名句:“因为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情感(情感,我们已经拥有得足够多了);诗更多的是经验。”
在里尔克看来,一首诗的诞生有赖于许多观察、感受、回想和思虑。而对情感和经验的析分,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和现代诗歌侧重点的一大不同。此后,情感不得不压低嗓音甚或戴上面具,以更幽深更微妙的方式出现在现代诗人笔下(自白派是另一种极致,情感又何尝不是一种经验)。
重视经验的人未必就能处理好诗,经验也不会自动转化为诗,它有赖于技巧。马克·肖勒的说法得到不少诗人学者的称许:“内容(经验)与完成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差距便是技巧。”我暂未找到原文,就译文来看,实在是好,尤其是指出把经验作为原始内容,把艺术作为经过作者锻造后的新内容。技巧是艺术的旋梯,是一个艰难而曼妙的过程,要仰仗思想,要通过字词,要尊重细节与偶然,要鲜新而惊异。
帕斯说:“诗人的经验中最主要的,是语言的经验;在诗中,每一种经验立即会取得语言的性质。”诗人的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世界、真实经验,一种是语言以及语言所“照亮”的经验和世界。对于诗人,还有一种残酷(也是美好),那就是唯有你写下了才意味着“真正”地经历和拥有,其间蕴含了审美、想象、虚构和赋形等。
经验是一己的私密,也是“流动的盛宴”,可以分为日常经验、审美经验,内在经验、外在经验等。理论家的说法很多,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视角和取舍。一些事实表明,人会因经验的丰富而匮乏。同时,经验又往往浓妆淡抹,需要辨认,尤其是第一次的辨认,即便已经被多次辨认、多次书写,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依旧需要像第一次辨认、第一次赋形一样去面对。
“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北岛感到汉语诗歌存在危机,“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人类的苦难经验”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无关”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指认。敏感的诗人往往注目于人类的苦难和人生的困境。人们尊敬那种自足纯然的诗,也颇为期待那些及时深入虎穴、勇敢担当的诗。北岛语气之激越,正可作为一种警醒。
在另一端,米沃什指出:“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生活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为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
至少从“恶之花”“荒原”等开始,人们在字里行间读到了太多对黑暗、罪恶的揭露、指控、批判,人们也有理由看到向上的、振奋的力,而且不应该是廉价的、空泛的。这样的崇高和力量,与奥登所言“呈上一支肯定的火焰”构成一种呼应,诗人有理由以自己的真诚和才情带来光亮、赞美和安慰。
经验是宝贵的,不过经验也并不都可靠,需要审视与锻造,同时,经验有着一种超越自身的本能,来自过去又带有未来性。所以,一方面不能经验主义,一方面也要信赖神奇而珍贵的“超验”的力量。诗歌是词语的又不止于词语,诗歌是经验的又不止于经验,总有更高的真实,更超越性的美与思。
回到曹有云的《经验之花》。这本诗集结构简明,直接以编年体分为4辑:经验之歌(2022)、个人简史(2023)、词语之轴(2024)、七星高照(2025)。
他的诗歌正是缘于经验与思考,笔下有雪,也有雪豹;有风,也有风情;有高原、高楼以及“高高低低的命运”。青海,西北,藏地,远方,空旷,辽阔,未知而真切,流动着多种可言不可言的身心体味。
他在《五十自叙》和《个人简史》中有类似的心绪:“我锋芒尽失、棱角全无/日渐破碎/日渐圆滑、精致/终究平庸成器、成物……/放弃了书写类似《伊利昂之歌》或者/《神圣的喜剧》那样的狂野梦想”,这样的话在现实中未必便于直言,而在诗歌中又不得不自我反思,当然其中也包含不甘与警策。
在国内外诗人里,海子和里尔克是他长久喜爱的两位,他们的优长以及与这个时代不同的气息也笼罩着他。他擅长的主要方式是抒情,有时是直抒胸臆,当然也有冥想、超现实等。
与此前的几本诗集类似,他还屡屡致意诸多文字艺术家:艾略特、史蒂文斯、曹雪芹、略萨、韩江……他们的经验与创见一点点感染他,推动他不断调试自己的诗学理念,“反对精致的/遣词造句/反对一本正经地抒情……/诗是初见……/要看到事物的尽头/看到核心地带令人心碎的空洞和苍白”(《反对》)
他打量着这个世界,“一堂深不可测的虚无课”(《四月》);“整整365集人间悲喜剧/终于压垮最后一根稻草”(《两条鱼》)。2023年,他写下《意义》一诗,“从锅碗和瓢盆无休止的碰撞中/聆听意义//从肉块和面条翻来覆去的煎熬蒸煮中/淬炼意义……”
他在多种细节和缥缈中寻觅意义。这令人想到早在2010年他便写有“紧攥词语之钢叉/搜寻意义之狐”(《生死旷野》),他并未展开究竟何为“意义之狐”,不过这4个字可以顾名思义,任君浮想。尤其是与“经验之花”相参照,或许,不妨借用古人互文的手法,易之为:经验之狐,意义之花。
经验是可感知的,也是隐秘的,甚至是狡黠的,魅惑变化的,期待着敏锐的猎手;意义也是狡黠的,游动的,却又仿若花朵,不依赖于人而又不断升起于人世,这花朵源自幽暗的根,以及比根更幽暗深厚的土地,并指向果实——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果实、成熟或无从成熟的果实。
与其以往的诗相比,迈入50岁关口的曹有云更敏感于美与困境,更多了从容与深沉,也更关注逻辑与对逻辑的打破,不断用实有也用虚空去试炼意义与可能。他身在西北而不时眺望大海,其汹涌,其博远,其自净精神,其苍茫未知。
从《经验之花》这部诗集,读者不难感受到一个诗人的惶惑与努力,对世界辽阔和自我局限的正视,对诗之为诗和生命之为生命的探勘。他的音调大多比较高,句子比较短。也许在整体或局部,音调不妨放低一些,句子放长一些,语速放缓一些,多一些叙事与省思,长短高低张弛、抒情叙事融合,会更具韧性与迷离。
美丑、善恶、经验超验、必然偶然、意义无意义……每个人都要穿行于高高低低的声音,领受那高高低低的命运。每当我们在雄心勃勃,在心灰意冷,在沉思创作,在为自己的无能、怯懦而懊恼不已时,天边照常升起也照常落下的太阳已经再度“完成了一幅辉煌巨作”。那是群峰之上,是大漠孤烟,是变幻的狐与花,也是无言无所不言的夜晚。
(《经验之花》,曹有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