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
应该是在成都红星路两旁的梧桐树还满目清凉的时候,青年小方来到了位于八十五号东三楼的《星星》编辑部。她的工作主要是责任校对,兼做行政、编务。
那时候,《星星》的元老杨牧、新泉、家发、刘滨功成名就,正在告退;后来,晓静、萧融、自国也相继告退;再后来,杨青、甘庭俭、干海兵、熊焱又有新的高就。《星星》营盘的流水一波接一波,每一波留下的浪花都是那么光亮。
当时,刚到编辑部的小方算是实实在在的晚辈。最开始来的小方不怎么写诗,校对和行政、编务跟写诗没有多大的关系。小方的尽职在于过手的校样省心,过手的行政、编务妥帖。在编辑部,“小方、小方”叫了十几年,有时候居然还一时卡顿,喊不出她“方志英”这个大名。相信省作协大院里像我这样的不少,哪怕如今的小方已不小。
我也退休多年了,退休以后就几乎再也没去八十五号的门庭,谨记为老要尊,不打扰,不去给他们添任何一点麻烦。知道小方写诗也不惊讶,先是在签《青年作家》《草堂》大样的时候读到,后来又在其他刊物陆续读到她的诗,零星的、成组的,有的还收入了我编选的《中国诗歌年度精选》。
我一直认为,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部,对于一个一心一意、心无旁骛的人,踏踏实实的人,就是一所学校,几年、十年、十几年耳濡目染,对于一个有心的人,不亚于读完本科、硕士、博士。其实,这个说法一点不夸张,原因很简单,清朝蘅塘退士在《唐诗三百首·序》说:“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个从专业诗歌刊物的校对干起来的小方,天天读诗叠加数以万计、数十万计,即使所读诗歌良莠不齐,或许正是这种良莠不齐,才逐渐有了判断、有了区分,久而久之也开始了写诗,并且还慢慢地自己写出了好诗,真是深感欣慰。
2024新年伊始,突然接到小方电话,声音怯怯地有点迟疑,问清楚了才知道她想出诗集,希望我能够为她的诗集鼓励鼓励。我几乎没有考虑手里的一大堆破事,一口应承了。说鼓励也不为过,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动。
我是断断续续读完诗集《折角与褒奖》的,随手记下一些感受,附录于后。诗集《折角与褒奖》是小方的一份别样的生命记录,她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观察、思忖和追问,呈现了自己数十年的生活智慧与收获。诗里丰富的意象世界,自普通和平凡里发掘、提取元素,传递出她宁静而从容的情感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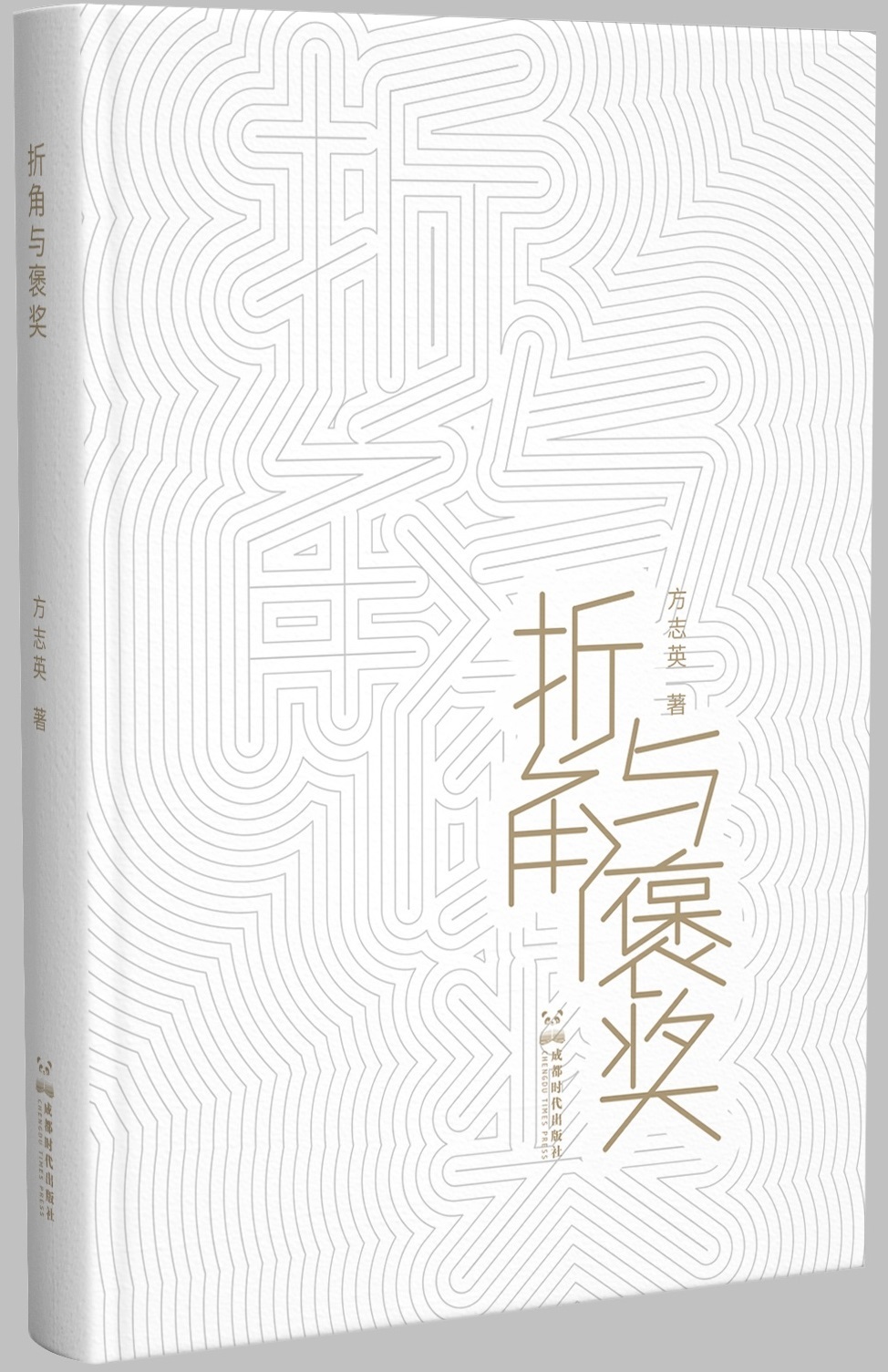
她诗中最多的具象和意象是女儿、父亲、母亲、祖母、祖父(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选了这些诗编入这本诗集)……他们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着诗人如何在这个浮躁的世间,慢条斯理地享受生活,如何在春花秋月中去奔赴。
“眉心的那颗痣/母亲给的/我得好好留着/等她老眼昏花时让她触摸着/还能把我认出来”(《痣或者志》),不仅表现出对母亲给予自己生命的感激,还显示出自己对命运的从容态度;在《父亲想去天安门》中,“我要带父亲去天安门/向左顾右盼的生活/向仓促的人世/我要/递呈这张蓄谋已久的请假条”,于过于平淡的生活中,诗人为了完成父亲去天安门的愿望,“蓄谋”已久;在《空与白》中,“你这省气象局高工,重庆妹儿/活着的时候很讲究/……我用饮水机里的热水为你擦脸/跟着医院的人,送你到太平间”,诗人写婆妈的一生,写亲人,无不透漏出亲人在诗人生命中的重量。
特别是,诗人总会在诸多诗中情不自禁地提及女儿,如写老院子,经过岁月的不断洗礼,老院子在变旧的同时,也承载了许多的记忆。“如今女儿远走他乡。小时候/总指葱为草,草坪上的草”(《有根的人》)。而这些具象和意象流淌的情感让人有了灵魂的撞击。
做编辑校对工作需要较真,是宁静而缓慢的,她的生活如此,从而诞生的诗歌也是如此,“折角”的痕迹便处处可见。
作为女性诗人,小方的诗也不难看出女性的细腻、精致和对世间万物的用心。正如华兹华斯认为“与一般人不同,因为具有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在小方的诗歌中可以感受到,她在极力探索、享受当下生活的同时,还不断地记录身边事物带给她轻微的战栗、诗意和交响。她感受四季的更替,将我们习焉不察的事物带入诗中,一种敏锐的、清新的、温暖的感觉便跃然纸上。
读小方的诗,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辽阔和生活的百转千回,以及生息的荡气回肠。因此,“群峰的眼里/我该是随遇而安的那一朵”。喇叭花、羊角花、衰苗、牙胡梯田、野菊花……在小方的笔下,一切物体都是复活的生命,都有平静的呼吸和艳丽的脸庞,就如同诗人“从中捕捉到了五指山的黎族人民/最耀眼的光焰”(《牙胡梯田》)。
诗人写春天,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在运用拟声词赋予内容童趣、可爱的同时,还给予春天以人物的特征和小动物的行为,“小姐,你还在枝杈间梦游么”“让靓仔的爪,老在你们身上挠痒痒”“你们按捺住内心的春意阑珊/可别冒犯他的天条,嘻嘻”(《春趣或者春问》)。
约瑟夫·沃顿曾说,以人格化手法“赋予物质的东西以生命和运动”,是“热烈奔放的想象的创造力”的产物。小方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大幅度的联想,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而辽阔,展现出诗人独特的观察和事物之间直接的联系。
红薯,是一种最常见的粗粮,是一种人们喜欢的主食。“从小至今,红薯就在我的心尖上/我爱她软糯如吻的甜蜜”。正因为熟悉、亲切和喜欢,所以诗人写自己眼中的红薯,“红薯叶唱着蝴蝶扑闪的音调/卷走了整块苍翠的田野和清风/蚯蚓、蜗牛和好看的瓢虫住在花箱里/它们是我童年的一部分”。
在小方的眼中,万物皆可入诗,万物皆是诗。一粒种子,也有前世今生,也能像人一样拥有七情六欲和悲欢离合,当“种子用拱出泥土的力量/走自己的路”时,诗人便“赞美生长的气息”。
行吟是诗人绕不开的题材,最大的忌讳就是走马观花,无病呻吟。古今中外优秀行吟诗篇精彩纷呈,别出心裁。小方深谙此道,唯有在留下自己深刻思考的地方才留下歌吟。尤其是早期的写李庄、水库、升钟湖、萝卜寨、草原等,写得活色生香,别开生面。
在《羊茸哈德》一诗中,她对羊茸哈德的宜人景色,和那里寻常百姓的心性与表情充满无限眷恋,这些鲜活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情愫对诗人的写作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藏寨新的重构里,我饱经/惊喜和赞美,着迷多彩的寂静”。诗人的故乡仁寿与异乡成都,一起构成了诗人生活中壮丽的风景。在《我与成都这座城市深情对望》中,诗人对春熙路地铁口出来后和红星路二段八十五号上的事物无比亲切,天空、鸟鸣、商标等每天停留在诗人上下班的路上,因此成都给诗人“诸多的可能和无限/像日出一样期许/像日落一样热爱”。
一个人写不写诗、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并不重要,一个人能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诗意很重要。在我看来,小方先是在自己生命中发现、找到了诗意,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不慌不忙地,让其成为吉光片羽成为诗。这就比那些为写诗而写诗,“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些诗人高尚得多,高级得多。
小方的诗,没有貌似高深的炫技,而是一以贯之的像是和读者心平气和的对话,说的是家常,可以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龙门阵”,也可以是隐秘的“私房话”,都是以普通生活的客观存在为基础。而这些“对话”在阅读上没有隔阂、没有“肠梗阻”,最终都转换成“人间烟火”。于是,她的诗歌见诸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等重要刊物和其他省级报刊,收入各类专辑和年度选本,还被转载。
《折角与褒奖》在编排上没有以内容或其他形式进行分辑,所编入的诗歌按创作时间的先后一气呵成。我们既能看出一个女性不断变化的思想,又能体会到诗人对生活的豁达、从容态度。我想,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小方的创作已经达到了其目的,朴素、真情,“使心灵得到改善、满足和愉快”。而且未来可期,不久的将来,我会继续读到小方更多更好的作品。
是为序。
(《折角与褒奖》,方志英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8月)
作者简介
梁平,重庆人,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从重庆调入成都,担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2016年起,担任成都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青年作家》主编、《草堂》诗刊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三十年河东》《近远近》(波兰语版)《汶川故事》《深呼吸》《家谱》《时间笔记》《忽冷忽热》《一蓑烟雨》等10多部、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长篇小说《朝天门》等。诗歌作品被翻译成美、英、法、德、日、波兰、保加利亚、韩、俄等语言。获第二届中华图书特别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四川文学奖、巴蜀文艺奖金奖等。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