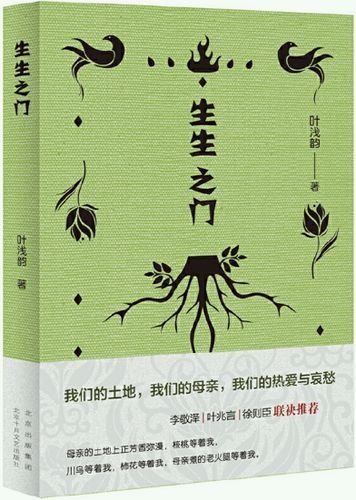
王刊
倘若要用两个字来概括叶浅韵的散文集《生生之门》(北京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我会选用“力量”。
叶浅韵有一个严苛的母亲,27岁时父亲猝死,后来家中遭遇火灾,奶奶也就在那几天去世。外公去世的那段时间,丈夫的生意出了问题,准备在宾馆了断一生。叶浅韵经历了人生里一段潜伏的黑暗,她“曾一次又一次地想杀死自己”。
叶浅韵生于云南的“四平村”,从中原往外丈量,那里显然属于边地,其“地域之灵”自然不同于被书香濡染和翻耕了几千年的土地。他们既与中原传统相接,而又从传统中溢出,自有其异象在——那种野性的,类似于大象在丛林间奔突的力量。
叶浅韵有限度地保留了那块土地上日常使用的语言,它们与书面语以一种恰当的比例混合,调制出了一种特质的钢筋,支撑起文字的大厦。
她避开“杀猪刀”,而要说“扦猪刀”。形容一个主妇应付不了的日子,她会用“抓不开”。对于扎实耐用的事物,“四平村”的人都用“石坨坨”这3个字。吃得心满意足时,会说吃得“舔嘴抹舌”。挣钱,要说“苦钱”。在土地上辛劳了一辈子,她写成“刨了一辈子”。儿子找母亲,她说“叫魂一样到处找妈”。叶浅韵家的火灾结束后,母亲挑着桶处理余火,一边哭,一边咒。咒大伯为何不好好在家照顾大妈,非要去街上收脚迹、还殃沙。这是骂人去死的恶毒话。
这些语言,读来像大象挥舞着象鼻,灵动而又能扛鼎。它们与普通话之间拉开了行距,多年来成为“四平村”进入世界的秘密,也是“四平村”人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比如雨水、火灾之类,唯一还能还手的“利”器。
为了配合力量感,叶浅韵选择了短句,又多用动词,读来像奔跑起来的象群,携风带尘,空谷传响。
如果说语言是一种习得和选择,那么进入《生生之门》的事件就是村里人不可抗拒的东西,比如火灾。三叔的儿子得了老母猪疯,一扯起来人都变形了,有一次没人在家,扯在火塘里,被活活烧死了。
同样祸起火塘的还有二舅。外婆才出门摘一把豆子的工夫,熟睡醒来的孩子就掉进火塘里。二舅的脸面目全非,五官都没有在正常的位置,嘴和胸脯扯连在一起,不自觉流淌的口水让他的身体常年有腐朽的异味。10个指头,被烧成两个变形的半拳,一直想握住什么,一直什么也握不住。害怕和害羞让他变得性格乖戾,他与他的羊群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挣扎在“活着”两个字里。外婆只要向外人开口这一句,我那个带残疾的儿嘛,就满脸泪水。她用一生的时间来护持她的二儿子,分开大儿子、小儿,自己带着二儿子讨生活。
这些悲剧发生在仓促之间,容不得人转身,被卷入其间的各方各有各的苦难。倘若要有个时间期限,那便是:一生。想一想,都苍凉。
同样是火,叶浅韵家的大院子发生火灾那次,一生三嫁的大妈被烧死在屋子里。她下半身被烧得没有了,道士用稻草做了一个假的下身,还她一个全尸。
同样是那把火,母亲“见到我,她把扁担往后一搁,坐在地上痛哭……天空灰暗暗的,冷叽叽的水钻进母亲的解放鞋里,钻进她的裤腿里,她全然没有了感觉。我脱下她的鞋子,血。我看见一鞋子里都是血,一枚锈钉子穿进鞋底进入她的脚底板,而她像是完全没了知觉”。
这些事实,坚硬如那枚锈钉子,在读者的心墙上猛敲。但它们其实不是目的本身,只是一个个接口,它们将通往更为宏大的事物,比如生命、命运、苦难、时间、土地……倘若只是一个个事实的陈列,那免不了贩卖苦难的嫌疑。而叶浅韵轻轻几笔,就带向了对事实的思考,有不解和质疑,也有对苦难的超越,显出与自然和命运抗争的乐趣。
二舅的一根手指在打工中被截掉了,“我”作为从村子里走出去的“能人”,参与到事件的解决中,但最后发现,“我”什么也没解决。于是,叶浅韵感慨:
“这个世界对待穷人的态度像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除了势利还是势利……我总是难免要把‘有感于斯文’写成‘有感于斯文扫地’。事实上,又何止是斯文扫地,生活常常让我感受到的是:斯文不如扫地。”
自己经历了从中兴到末路,经历了背后的冷眼和投枪后,叶浅韵写道:“也唯有真正经历过大名大利的人,才有资格谈淡薄名利。”
不管土地如何以痛吻我,而“我”却报之以歌。
“土地和母亲,都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母体。只愿我们在挣脱她的怀抱时,眼睛里还有慈爱,心中还有敬畏。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如今,我的身体正在向大地弯曲。我努力地活着,像母亲那样,做一个热爱土地的人。以期让自己有一天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时,能与土地的干净相匹配。”
这样的思考和感慨何其多,让人觉得叶浅韵是一个用脑袋丈量大地的人。正是这种沉思的力量,击穿了语言和事件的坚硬外壳,通向更为高远的玉宇琼楼。
正是有了那样的“地域之灵”,那样的家庭,才会锻造出具有那样思考力的叶浅韵。叶浅韵没有浪费这一切,她把那块“地域之灵”的盛产都收聚起来,团成一团,在文字里一一释放。她像迁徙的象群,冲破原有的栖息地,所经之处,草木摇落,露水为霜。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