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
向以鲜的散文集《两朝诗影》,带我们进入了公元7—13世纪的时刻。那个在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时代,前人已将诗心调度得或柔媚生姿,或铿锵悲怆,或深入骨髓。向以鲜用一根彩绳串起,以诗人、诗事、诗典为经纬,把千古佳作在中国文脉中留下的剪影、侧影、倒影、掠影甚或幻影,编织出彩云朵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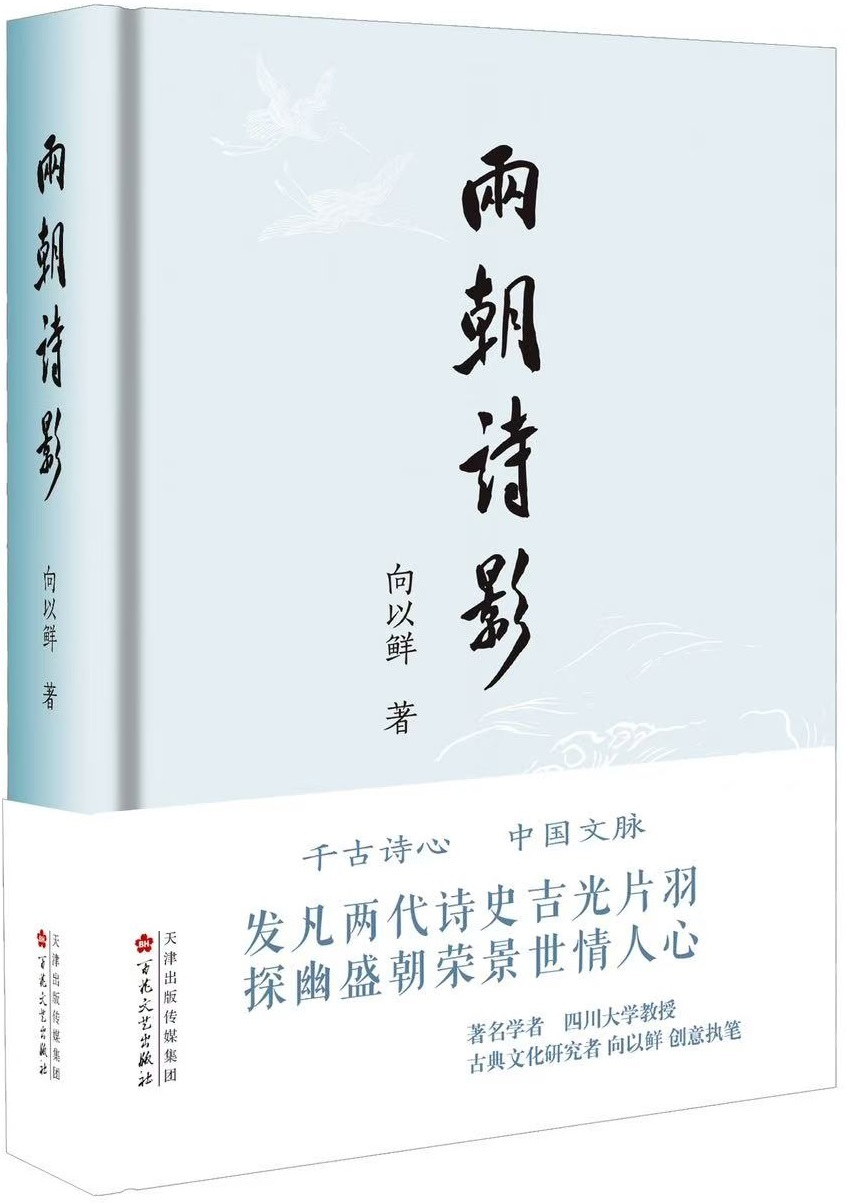
阅读《两朝诗影》,要有艺术、哲学、美学、历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储备,还要具备辨析能力。读《两朝诗影》里引述的诗句,那悠远的两朝气息,各路英雄们或辉煌或落寞的一生,从记忆中复活。
在《我家江水初发源》《春梦或西方》中,特意将苏东坡织入篇章肌理,是作者字斟句酌的有心之举。《春梦或西方》跳出单纯的史料铺陈,在历史叙事与人文思考间寻得平衡,直抵生命哲学的深处。《我家江水初发源》仅几千字,将东坡关键的几年和最美的词道尽,把东坡的精神气质写得透彻。
草堂雨夜,杜甫静听润物雨声,畅想晓来锦官城繁花带露,挥就《春夜喜雨》。在《喜雨札谭》中,作者逐字释析,甚至连“花重锦官城”之“重”的多音读法都做了细究。即使这样仍不尽意,引出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的见解:“雨骤风狂,亦足损物……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为这份共鸣添一笔佐证。
从40年前跟从导师系统学习唐宋文学,到古代典籍的校点与整理,再到教化育人的大学教授,在古典文学中沉浮酝酿几十载,向以鲜感慨:“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字能禁得住推敲。”
在后记中,他写道,《两朝诗影》以一事一物为切口,不止珠联诗文丽影、璧合诗词群英,重要的是,它以个个散点,透视唐宋文明的盛世荣景,更勾勒出存身其中的两朝生民的生态与心念。
引述历史材料做文章,作者的文字叙述不是被历史牵着鼻子走,而是以轻盈的笔触洗去历史沉重与凝滞的一面,以不被理性桎梏且有着如梦幻般想象力的文字,与纵贯逾千年的代表性与特征性的文化衔接呼应,联络得恰到好处。
这样的书写方式拆解了时间与空间理应千万的距离,带有切肤温情。语句片段,脉络清晰,过渡自然,掌故鲜活,周折曲转,在无限的可能性里,加入见解或猜测,把我们带入无以言说的诗境,又把我们带出唐宋两朝时空。
李敬泽谈到作家评论他的《青鸟故事集》有意义时说:“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这句话也是为《两朝诗影》量身定做的注脚。李敬泽的意思其实是说,一个单纯的学者,可写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
“古籍整理是一种十分传统的坐冷板凳工作,如何平衡枯燥与诗意的天秤?又如何在发霉变黄的典籍中发现现代性诗意?其实,任何事物中都饱含诗意和现代性。孟子说得好,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诗意和现代性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存在于春花秋月、爱恨离愁、玄学思辨或后工业文明景观中。不,不是这样的,诗意和现代性的存在边际远远超出我们的心力所能企及之地。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翻阅古代典籍时写出来的。”可以想象,作者翻动泛黄书页,对典籍中那些藏在字缝间的细小动因,怀抱着近乎本能的敏感。
读到《胡姬魅影》一章,我骤然一惊,原来这篇文字早在两年前读过,而且在我写的《编辑手记:文字对着真与善》,还摘取了最后一段:“横贯中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不仅给中国的大唐带来自由、开放和繁荣,也带来了气象万千的异质文化。穿行其间的胡姬,如同穿花的蛱蝶或翠鸟,作为一种肉体之美的存在,为唐代诗歌舒展、幻化、催生出璀璨的、令人意醉神迷的万千魅影。”
让我们回到李白的《少年行》吧,那样的韶光时代,那样的得意扬扬,那样的旁若无人,那样的纯粹和放纵:“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真的找不出比这句子更美的了。一部好小说,往往在结束的时候,又昭示着新的开始。诗影昭昭的散文集《两朝诗影》亦是这般,那样的韶光时代,那样的纯粹和本真,闪着真金白银般的光。
(《两朝诗影》,向以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