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遵投辖”这个不算常用的成语,记载的是汉代官员陈遵为留宾客畅饮,将客人车辖投入井中的典故。后世诗人时常化用这个典故,如杜甫的“甘从投辖饮,肯作置书邮”。更鲜有人知的是,在投辖留客之后,陈遵的仕途还因一次宴饮一度停滞。
王莽时期,陈遵官至河南太守,他与身为荆州牧的弟弟陈级一起路过长安富豪左家,不久就被司直陈崇弹劾,称陈遵在寡妇左阿君那里醉酒夜宿,“湛酒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恶不可忍闻”。在陈崇的力主罢免下,陈遵被罢免了官职,直到很久以后,才“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
陈遵因“醉宿寡妇处”而黯然去职,这正是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免官制度的一个碎片。
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邓苗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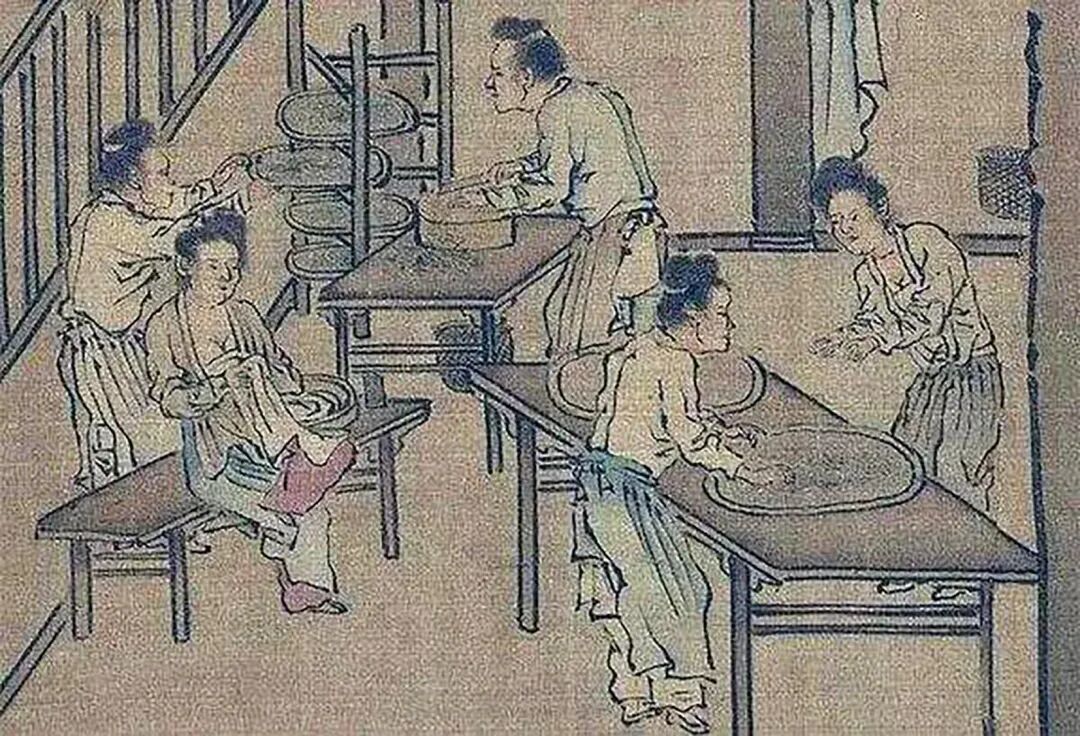 唐代律法中有“妻无七出”条,如果没有“七出”“义绝”这样的法定理由,丈夫要与妻子离婚,就要受到惩处。
唐代律法中有“妻无七出”条,如果没有“七出”“义绝”这样的法定理由,丈夫要与妻子离婚,就要受到惩处。
不守立身之德
陈遵身处的汉代,是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逐渐成形完善的时代,官员选拔、任用、考核、晋升、黜免都有了一整套运作体制,对官员的管理,并不局限于官场上的表现,而是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了考察之中,稍有不慎就会招致罢免。陈遵的豪放不羁,在私人场合也许是魅力,比如他被罢官后,“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反而声名更旺,但在官员身份下,这便成了需要被制度规训的“失德”行为。
比“失德”更严重的则是违法犯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
唐代律法中有“妻无七出”条,如果没有“七出”“义绝”这样的法定理由,丈夫要与妻子离婚,就要受到惩处。这是针对当时所有婚姻关系的,最高有“徒一年半”或“杖一百”的量刑。有官员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户部尚书李元素在任郎官时,原配妻子去世,续娶出身琅琊的王氏为妻,但后来李元素宠幸仆妾,又被人怂恿,要与王氏离婚,王氏妻族便上诉。
唐宪宗《停户部尚书李元素官诏》中提到,李元素的行为“岂惟王氏受辱,实亦朝情尽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最终,李元素不仅被免官,还被罚向王氏赔偿五千贯钱。
李元素所违之法还属民事范畴,如果作奸犯科,触犯刑事,官员同样会面临免官的处罚。北魏时,大臣裴瑜就因“虐暴杀人免官”,汝南王元悦也“坐杀人免官”。而在律法相对完善的唐代,“免官”在《唐律疏议·名例律》中单列了一条,规定“诸犯奸、盗、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并谓断徒以上);若犯流、徒,狱成逃走;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及婚娶者:免官。谓二官并免。爵及降所不至者,听留”。
《新唐书》记载,监军王定远擅杀不服从他的军将彭令茵,并将尸体“埋马矢中”,彭令茵的家人请求归还尸体,王定远也拒绝。这种恶劣的行径引起了河东全军上下的愤怒,长期受制于王定远的河东节度留后李说便将此事告发给唐德宗,“德宗以奉天扈从功,恕死免官”。本来按照律法,王定远的行为足以被处死刑,但“监军有印自定远始”,重用宦官监军的唐德宗还是留了王定远一命,仅以免官处置。后来,不甘心的王定远刺杀李说失败,又矫诏败露,“召麾下皆不至”,最后戏剧性地从城楼上坠亡。
不过在不同时期,免官一词的含义也有变化,类似的还有“免所居官”。有时免官指的职事与勋官同免,有时则不然。比如有学者指出,“六朝的免官不过免所居职官而已,兼领之官不在免例;而且职事官被罢免之后,文武加官照旧保留:‘有罪应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职官。’”像《唐律疏议》“免官”条中,就特意提到了“二官并免”。
相对来说,“除名”的含义更明确一些,也是更严苛的处理方式,大多指的官员因罪被彻底清除出官员的行列,成为庶民,类似的说法还有“除名勒停”“除籍”“削籍”“免为庶人”“革职为民”等。这样的处置往往涉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唐律疏议·名例律》“除名”条规定:“诸犯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未尽人臣之责
无论是私德缺失还是杀人诽谤这类的违法犯罪,侧重点更在于公职之外。对于官员来说,在履职过程中,因失职或渎职被免官,也相当普遍。失职或渎职虽然主客观因素和影响程度不一,但都可被归为“未尽人臣之责”。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废免不称职官员的说法。《管子·明法解》指出,“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胜任者为官,失职者离开官员队伍,这是维持国家治理的要求。对于古代官场来说,官员失职行为遍及行政、军事与司法等多个层面,免官是一种能灵活运用的处罚,哪怕没有条例明确规定哪种失职、渎职行为应当免官。
唐总章元年(668年),曾任雍州司功参军的崔擢犯事了,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向朝廷举报了一条线索,说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李乾祐曾推荐自己当尚书郎,虽然没成功但李乾祐私下告诉了自己,如今他要检举李乾祐“泄禁中语”。所谓“中语”,指的是宫中例不外传的言语、机密,尤其包括皇帝的话。作为朝中重臣,李乾祐私下向他人泄露官员晋升的人事机密是大忌。很快,“强直有器干”的李乾祐得到了免官的处分。
而在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领域,惩罚也十分严厉。唐高宗显庆年间,左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征讨西突厥,因“逗留失军期,追贼不及”被免官。值得一提的是,程知节是唐朝开国功臣,他不仅追随李世民平定各方割据,还在玄武门之变中有拥立之功,因此在免官的处分前,还多加了“减死”二字。不过很快程知节又获起用,被唐高宗授予岐州刺史。武则天时期的韦待价就没这么好运了,永昌元年(689年),身为右相的韦待价奉命讨伐吐蕃,却“迟留不进”又“会天大雪”,最后“士卒多饥馑而死”。回朝后,韦待价被除名,配流绣州,很快去世。
失职之责同样贯穿于日常的地方治理中。《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称吏部所选县令多不合格,唐玄宗便将这些新选出的两百多名县令全部召来,亲自策问,“不能对者悉免官”,还没正式上任就被拦在了门槛之外。还有明代庐州府的地方官员,万历三年(1575年),因庐州府发生六名贼犯越狱的事件,作为主管官员,程杲被“革职为民”,白希珩亦受惩处,诠释了“不胜其任者废免”。
除了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也有因贪污腐败被免官或除名的。在古代特殊的官场环境中,贪污腐败的处理后果有大有小,往往视统治者的需要“灵活调整”。同样是贪腐,有的官员身死家破,有的官员却仍能青云直上,当然也有官员被贬官、免官甚至除名。
 唐高宗显庆年间,左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征讨西突厥,因“逗留失军期,追贼不及”被免官。
唐高宗显庆年间,左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征讨西突厥,因“逗留失军期,追贼不及”被免官。
北魏时期,孝文帝元宏即位后,安排幽州中正阳尼出任幽州平北府长史,兼任渔阳太守,没想到还没上任,阳尼就因任中正时受乡人财货而遭免官。后来,每每想起,阳尼都黯然神伤,感叹道:“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与本何异?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
唐代元和年间,唐宪宗先后平定河北藩镇叛乱,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史称“元和中兴”。这一时期,朝廷对地方官员监守自盗、贪赃枉法的处罚也相对严格。元和十二年(817年),郑州刺史崔祝因“擅出州仓粟麦,贵货之,以利入己”被除名,后又“锢身配流康州”。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有时在宣布对官员的除名处分外,还会在后面增加“永不收叙”“永不叙用”等表述,比如《大明律·刑律》规定,“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
但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下,实际上这些官员还是有相当多的机会起复的,这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和统治者的意愿。清人陆心源撰写的传记合集《元祐党人传》中记载,梁安国在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因“上书谤讪”,“勒停,永不收叙”,然而仅仅两年后,他就“叙复宣义郎”。
难逃时势之局
西汉中后期,有一种独特的免官现象,就是“以灾异策免三公”。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汉代一些人认为,灾异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灾异发生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不满。所谓三公因灾异被免官,指的就是每当灾异发生,皇帝便甩锅给三公,通过三公免官甚至自裁来替自己承担上天的怒火。
比如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日清亡光”,汉元帝下诏问责,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被迫上书乞骸骨,汉元帝“乃赐金车马,罢就第”。
表面上是三公主动请辞,实际与皇帝罢免无异,而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局了。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荧惑守心”,有人提出“大臣宜当之”,汉成帝随即召见丞相翟方进。不料,翟方进似乎并未领会汉成帝的意思,“还归”。没有等到翟方进自请罢免或自杀,汉成帝又赐册,将自己登基十年来灾害频发、百姓饥饿、盗贼肆虐、官员怀奸朋党的过错全推到翟方进身上,还说“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反复让翟方进反思,就差明示他自裁以谢天下了。在汉成帝的咄咄逼人下,翟方进别无选择,以自杀了结。
这样的免官,显然不是因为官员本身不称职或违法犯罪,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太冤了。东汉时期就有官员写《上疏谏因灾异免三公》,反对这种现象。
实际上,在古代官场中,有大量的免官、除名、革职都发生在政治斗争之下,官职的去留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自身的德行与能力,官员个人命运往往难逃时势大局的倾轧。比如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朝散郎宋昭上书谏北伐,引起当政的王黼不快,随即被除名勒停。
在宋代,党争频繁,免官、除名也成为政敌之间互相倾轧的工具。庆历四年(1044年),进奏院官员苏舜钦与同僚用“鬻故纸公钱”(卖废纸的钱)饮宴,结果被太子中书舍人李定告发给御史中丞王拱辰。王拱辰立即上奏弹劾,称苏舜钦等人“监主自盗”,用变卖公家财物的钱吃喝,并在宴会上作诗冒犯圣上。此事越闹越大,最终,苏舜钦、刘巽被除名勒停,王益柔被降职,其余人也被降职或贬谪。
进奏院事件之所以争议不断,就在于其后有党争的影子。事件发生时,正值庆历新政,苏舜钦与“革新派”关系密切,而王拱辰则是反对庆历新政者。相传,苏舜钦等人被处分后,王拱辰喜形于色,说“吾一举网尽之矣!”可见苏舜钦的行为虽算不上无辜,但无疑被放大了,更令人唏嘘的是,苏舜钦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没有等来“叙用”。以苏舜钦的政治履历、社会名望、人脉关系,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
当稳固政权需要替罪羊时,三公可因天灾而引咎;当党争需要清除异己时,名士亦可因小事而万劫不复。本该服务于澄清吏治的“退出机制”,在绝对的政治权力与不断变幻的时势面前,最终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这是积重难返的古代官场难以避免的结局。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