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大巴山是一条与秦岭几乎平行的山脉,但它的名气没有秦岭那样大。大巴山西接昆仑山,一直延伸到三峡神农架,与长江对岸的湘西黔北的山脉相连,绕一圈就和青藏高原把四川盆地包裹在中间了。
大巴山南麓,嘉陵江、涪江与巴河、州河之间的一片地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川北。由于地域原因,在天下分裂的时期,汉中成了秦岭和大巴山、关中与西蜀之间的跳板,而跳板面前的川北就成了一片被反复争夺的征战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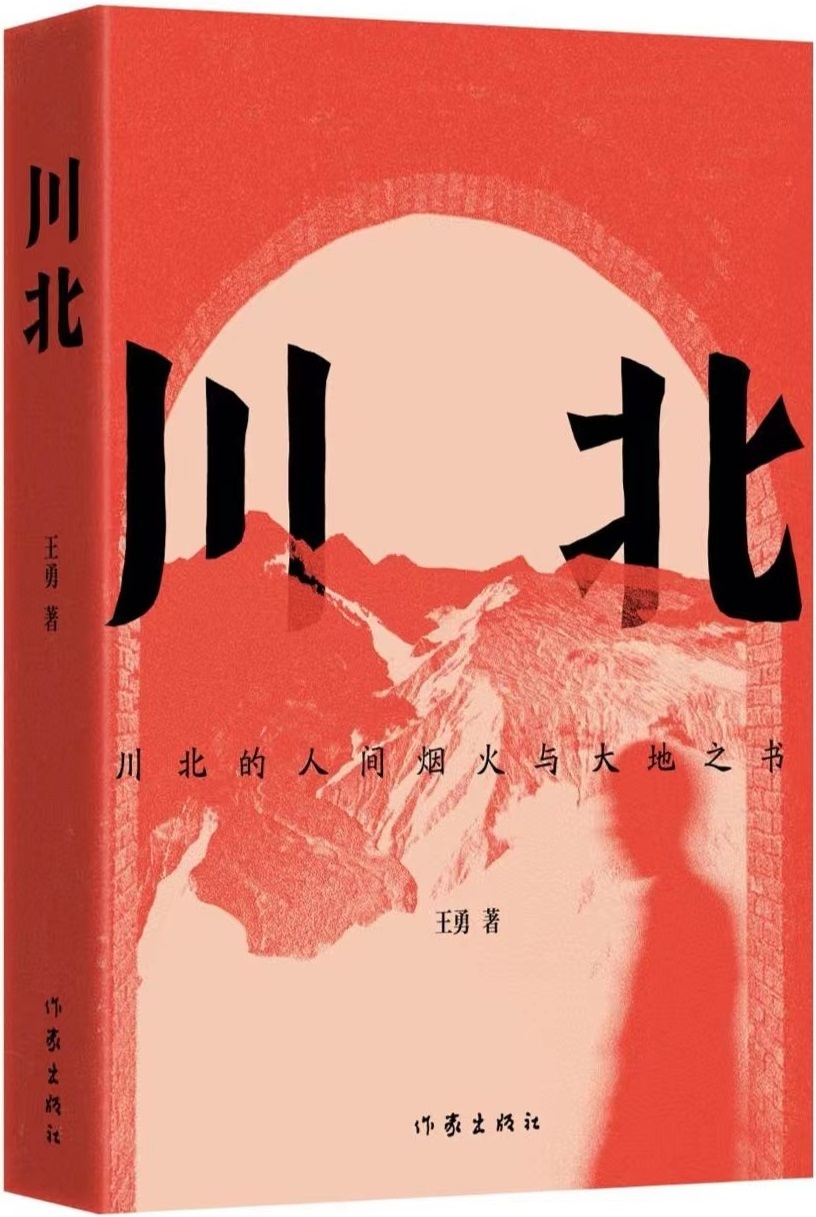
萌生写一部关于川北的小说的想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可谓多年前的一个梦想。我从小就生活在大巴山的乡野,在那里读书和劳作,在那里经历生活的磨难坎坷与少年的忧伤孤独。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读上了文学狂热年代十二分红火的中文专业。
我听到过那片土地上无数口传的生动故事与民歌,后来工作的全部时间也耗在了那片地域,大半个世纪我都没有走出川北。自参加工作起,我尽力把少有的闲余时间用在了在川北土地上行走。因此我熟悉川北的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乃至很多村,见过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收集和听闻了无数的奇闻轶事。越是如此,越觉得非写出一部书不可。
尤其是到了近年,知悉这片土地历史的一代代人已经衰老或故去。我不能让这片土地上那些生动的过往,那些饱满的激情与倔强的忍耐,无声无息地湮灭于地下。我要让土地说话,述说那连绵的苦难与不屈。
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与跑一场马拉松一样,要的不仅是耐力,更要的是体力。工作原因,难得有大段时间静心写作,所以本书动笔的时间比较早,却一直写得不那么顺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
直到近年,反而工作越繁重辛劳,写作的思路越流畅。我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写作,消耗了数千张纸,数百支笔,总算完成了70多万字的书稿,最后成型的这部书缩减到60多万字。
无论作品写得好坏,我坚持下来了。直到2023年秋分的晚上,敲完作品的最后一个字,我对着窗外的天空和青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无所谓喜悦,无所谓忧伤,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但我的眼眶确实湿润了,我为自己的坚持与顽强而感动,我终于制造出了一块硕大粗笨的“砖头”,完成了这样一部告慰川北大地的书。幸运的是,书稿顺利入选四川省作家协会2024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更增加了我要尽快将此书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自信。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为写作本书,我阅读了大量文史资料、族谱乃至民间野史、医书、巫术、堪舆、碑文,进行了大量田间调查与走访,力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采用以点带面、以小写大的结构,通过川北大巴山下桃花湾一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繁衍历程,让土地陈述川北的故事。
翻开川北所在的近代史,这里有农耕社会的日常,有淳朴古雅的民风,有乱世里的爱情,也有为所欲为的草菅人命,更有时代迭变的波诡云谲。
仁义礼智,忠孝廉耻,压抑与放纵,坚韧与挣扎,朴实与狡黠,倾轧与杀伐,苦难与良知,生养繁衍,爱恨情仇,一切都在时变境迁中洗澈沉浮,滤浊澄清。人间的苦痛、纠结与忍耐、欲望都饱含于这一片大地的泥土中。
由于读书的驳杂,我的作品里既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影子,也有苏俄批判现实主义、欧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子。我在熬制川北味道的麻辣火锅,小说故事跨度50年,情节复杂,人物纷繁,现实与魔幻,牧歌与史诗,粗放与细腻,精雕细琢与浓墨重彩,大量风物、习俗、民歌有意识地加入,构成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画卷。
那些生长故事的乡土正在远去,流逝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远影,消失的总有几分怀念。后来人如能通过读这部书知晓川北大地的过往与曾经,我亦感足矣。
(《川北》,王勇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