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安然的诗歌多以内蒙古草原风情作为审美范式,体现出了地域诗学的生产性。这样的写作既具有回应当下城市书写的乡愁意识,也不乏通过回忆草原生活而拓展异质经验的美学向度。
在安然的诗歌中,牧场、秋草、马匹,包括坝上与湖泊,皆为真实生活经验的诗学表征。它们作为不断出现的语词意象和地理景观,构成安然诗歌极具辨识度的质感。那种空间的辽阔所带来的旷达与渺远,也形塑了当下青年诗人抒情诗写作的独特面向。
在新诗集《正在醒来的某个早晨》中,安然一如既往地以地域体验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在完成身体位移和心理迁徙的同时,也建构了从北方到南方生活的诗人独特的精神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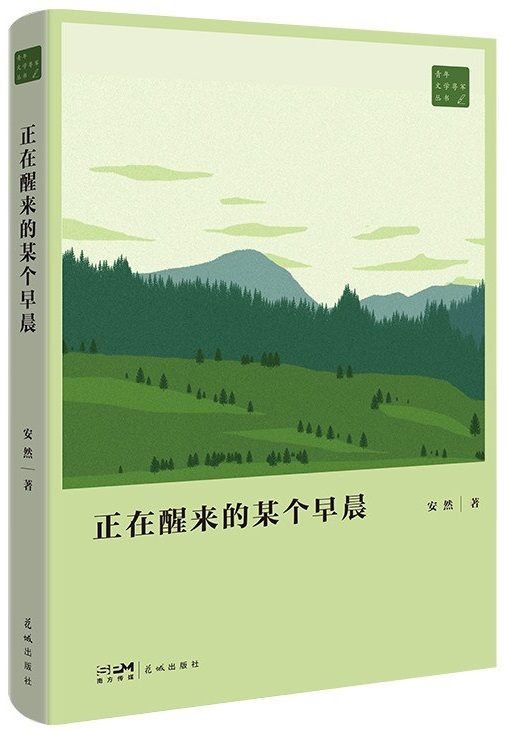
她在抽丝剥茧般的层层深入中凝视生活,并以抒情的升华确立对观看经验和人生领悟的主体认同感。安然并没有在贩卖私密经验的书写中寻求抒情的动力,相反,她以更干净的方式延续了很多人放弃的故乡书写传统。
一方面,诗人在贴近自然中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这里既有亲历者的体验和感受,又有想象的超现实主义意味;另一方面,安然并不刻意追求先锋的实验性书写,她选择重新回到浪漫主义抒情中,去发现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除钟情于“我身体里的草原”和“母亲河之歌”,安然以打破惯常符号化的笔触消解那些怪异的表达,反复再现生活中灵魂出窍般的启悟。
“我每日写诗,日子往下落/一个人忏悔,等待惨痛的结局/从此生活就有了深意……//是什么在救赎人类/我每日写诗,在诗歌中问责/在诗歌中修正自我”(《活着》)。诗人将“活着”转化为“生活”的另一面,这些生活经验通过诗人的转换与变形,似乎具有一种仪式感。生活并没有被琐碎经验所瓦解,相反,它内在地构成了我们理解自我与时代的镜像。虽然诗人也写了《日子》《致生活》等诗,但她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有着独到的“问题意识”。
从草原上走来的诗人,他们的开阔与大气源于骨子里对远方的向往。很多时候,他们也使用大词来表达对现实的关切。在安然的诗歌里,她并非刻意使用那些大词,她恰恰在更深邃的时空转换中,激活了记忆与想象的潜能,以更具张力的词语组合,呼应生活中出现的错位与反差。
“我在人间受伤了,整个世界跟我/一起接受阿斯匹林的治疗/我在人间受伤了/整个世界跟我一起休克在山丘和沼泽”(《在人间》)。这种宏大抒情是基于诗人对生活所持有的悲剧性审视,其大开大合的书写折射出安然切入诗歌的幻化视角:诗歌不是对生活经验的复制与照搬,而是以更具创造性的表达,重新命名人生的诗意。
从内蒙古到广州,安然一直致力于书写这种迁徙带来的微妙变化,这本身就内化于不同地域的生活经验对写作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她的写作也带有“元诗”色彩,即以感悟人生的表达,来意指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则,甚至还有着某种隐喻意味。
她这样书写在广州的生活:“我每天编书、写诗,按时站地铁/……在一个人的小房间反省/在城里,我是这般活着”(《这般活着》)。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她会以更写实的方式严肃地对待“活着”的悲剧性。在安然这里,她强化了生活的现实感,但她不是以抱怨的方式宣泄情绪,而是在更高的维度上对生活与写作进行美学定位。
为什么诗人如此强调生活的当下性?无论是对日常进行记录,还是对远方进行想象,其实都伴随着真诚的道义之感。“我一直想要这样的生活/云在檐上,水在远方/豌豆苗在园中应允一场大雨/而远方,有一簇簇的小花竞相盛开”(《生活素描》)。这是理想中的田园乌托邦,恬静的生活背后,反映的是诗人对待诗歌和人生的态度。在她看来,诗歌有着高于生活的另一面,有着我们无法抵达的境界。当然,诗人与生活的互动,其前提在于她热爱生活,不管这生活是具体的物事,还是抽象的精神,它仍然是对我们平淡日常的调节。
“此刻,你开始诵读,并告诉/周围的人,你不再恐惧/失意、落入深渊/你开始热爱拥有、绿色/植物,和诗歌”(《热爱生活》)。它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总能在特殊时刻影响我们的心境;它们经常被我们所忽略,但又意外地为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并将其还原为一种线性时间延长线上的诗意转化过程。
也正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安然的诗歌被赋予浪漫主义的美学格调。她一方面强化在当下写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于诗的层面恢复其生活书写的内在价值秩序。她有时热衷于傍晚写作,有时又精准到6点钟写诗,这种直面写作时间的当下性,不是一般符号学意义上的诗学建构,而是要“用尽气力”去改造与转化生活的可能性。
由此,安然为自己的诗歌确立了一种象征色彩。她在与生活的周旋中,既复原了为人生写作的本意,也在挑战中探索诗歌的未来空间。
(《正在醒来的某个早晨》,安然著,花城出版社,2023年12月)
作者简介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