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
孜格,一个有意思的笔名,早年大学校园的卫星湖就留下了他青葱的分行。我和他是校友,只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在卫星湖遗憾地前后错过。很多年以后,在一次校友的聚会上,确认了这个脸上几乎没有年龄印记的小师弟。一堆与他同年级甚至同班的同学们,多少都有了岁月的沧桑,而他安静、温和、节制的言谈举止,恍若刚离开校园不久,上天对他的偏爱为他挽留了青春的容颜。其时,他已经在一个地方党政部门有过多个供职。我原以为,从学校出来以后,他的职业生涯节奏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诗意,应该和很多人一样,与诗歌渐行渐远。然而错了,当我拿到他的诗稿《太阳云与绿皮火车》,看到他每一首诗留下的写作时间,才知道诗歌在他内心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他一直恪守对诗歌的虔诚,一直精心呵护生命里延绵的诗意,诗歌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份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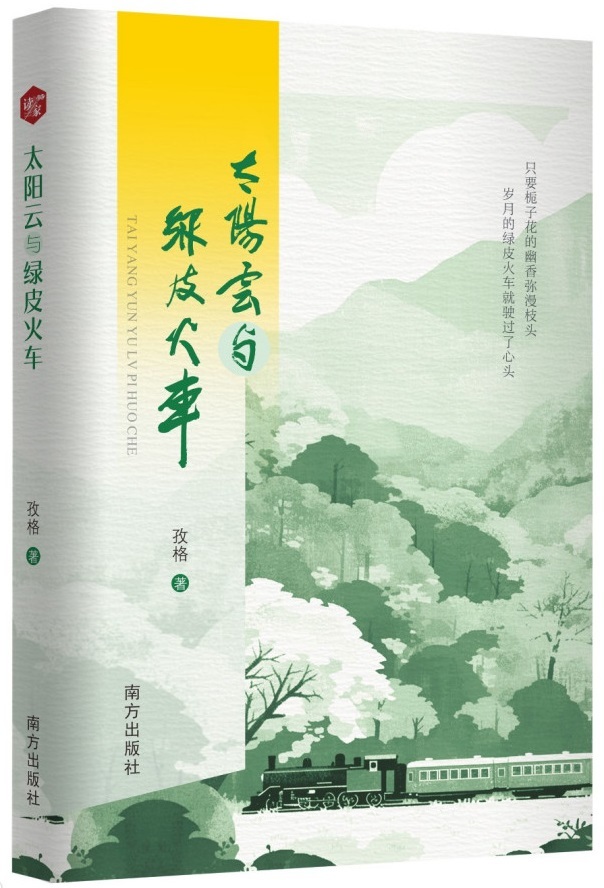
与其他人写诗不一样的是,孜格写诗这么多年并不在乎发表,而是在记录自己对人、对事、对人生思考和对世界认知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记录显然比年复一年的年度总结,或者日渐丰满的个人履历,更有时间的认可和留存的价值。所以孜格写诗就少了很多功利,他的诗歌能够让我们看见活生生的人,以及与之必然发生关系的生活的林林总总。“当脸上不再有无邪的笑容/在孤灯野火中踽踽前行的我/正追寻无边的星云”(《三十而立》),这是诗人生命的前行,心里只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没有边界。
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或者说为什么与生俱来,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份诗意,在孜格这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孔子曾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的所愿、所想、所感,并不是适合任何方式的表达,而只有诗歌可以示人天真磊落。古往今来,凡是能被成为“诗”的,无不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这是一种高贵、智慧的精神指引。诗歌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不仅仅是肉体的温饱,还需要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安顿,而诗正是人类精神寄托和心灵安顿最恰当的方式。我们今天能够在光怪陆离的包围之中,在忙忙碌碌的奔波之余,稍稍停顿片刻,在静夜,以一首诗品味一缕温暖的微光,找到一丝清凉的慰藉,就不会再去计较已经过去或者刚刚到来的纷扰。唯有此刻,可以安顿自己躁动不宁的内心。
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有太多的不正常,岁月静好奢侈得遥不可及。我相信每个人在“不正常”的状态下,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挣扎、逃离和摆脱,而只有还乡,哪怕回忆,哪怕想起,才是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只要筷头挑起几根鲜面条/就会想起流离的张飞庙/不知他是否还盼/思绪重回躯体的嘉陵江//想万里的长江/准备就此浩浩荡荡//想登云的步梯/是否真能穿越云巅之上//还有沉睡太久的恐龙兄/要小心翼翼的哦/把它的梦下载到课堂//绝壁的龙缸,狭长的地缝/龙洞流淌明月光//三峡之上,天生云阳/一碗小面盛得下故乡”,这是孜格的《想云阳》。云阳是孜格的故乡,在重庆,故乡富饶的历史与人文在身体里的蛰伏无论时间过了多久,只需要几根面条就能够满血复活。
孜格的另一首《岁月的绿皮火车驶过心头》:“只要栀子花的幽香弥满枝桠/岁月的绿皮火车就驶过了心头//比如熙熙攘攘的站台/人头起伏的麻花辫/比如习题集内/一片精彩的嫩叶藏在答案里/猛一回首,太阳花/也会瞥见你长长的睫毛/不如望着窗外/闭上眼/只要栀子花的幽香弥满枝桠/岁月的绿皮火车就驶过了心头”。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被他强烈地带入,栀子花、绿皮火车,站台,熙熙攘攘的人头,麻花辫、年少的作业本,习题里夹着的嫩叶,因为再也看不见的绿皮火车总会驶过心头,这一切都清晰如昨被带了出来。看不够,不敢多看,“不如望着窗外/闭上眼”,否则一定是眼泪如注。我注意到了这首诗的首尾两句,是完全重复的,这种重复的句式在诗歌里是应该避讳的,但在这里不仅没有多余的感觉,反而对挥之不去的乡愁做了更为浓烈的强调。
孜格的诗除了密集的乡愁,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敏感。诗集《太阳云与绿皮火车》,书写大自然的篇什不在少数,难能可贵的是,孜格眼里的大自然不是浮光掠影的湖光山色,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有思考、有暖意地把大自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把自己的情感和身体与大自然合二为一:
立春
残冬还没有来得及
脱掉冰冷的外衣
沿着雪逃逸的痕迹
盘旋而上
把自己缩为雪山的一粒寿司
用你的手触碰历史
捧一把唐朝的雪吧
也许还残留杜甫的一丝傲气
窗含是不够深情的
千秋的转换
只在此时
——《唐朝雪》
写雪的诗比比皆是,而孜格的这首《唐朝雪》,写得别致,写出了大容量、大情怀,让人读了心生喜欢。他没有着意描摹雪的自然状态,他看到的西岭雪山的雪,已经不是眼前人人能看见的雪,而是主观的雪,个别的雪。一首短诗的长度和宽度给人以惊喜。时间被他拉长在唐朝,与那个时候的杜甫有了关系,产生了共鸣。而这个共鸣使得这雪有了历史的纵深感,有了古代文人的气节与风骨,这也是作者所崇尚的的气节和风骨。这首诗从技术层面上看,朴素、节制,不露痕迹地呈现,收放自如。放得开,放到了千年以前;收得回来,收到了“只在此时”。
诗集《太阳云与绿皮火车》里,有一首《丁真的世界》,一个在网络蹿红的普普通通的少年,从来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少年,他难以置信的简单被遇见、被传播,足以让所有关注的眼睛潮湿。“蓝天剥落的璞玉/在格聂湖溅起的一抹浪花……丁真的世界很小/小得只剩下白马,白塔/寺庙与村庄/从来没有抚摸过轮滑/秀秀、香奈尔与普拉达//丁真的时光很慢/时针被冰川所羽化/牛、羊、人/在草地上与阳光同床/最快的节奏/雪山下与朋友们赛马//丁真的世界很大/大得没有边界/那匹小马蹄下的芳草/已是天涯”。这首诗像一幅素描,没有主观,只有客观,只有不动声色的客观,却把一个花季少年大和小的生存状态勾勒出来。作者没有去指指点点说长道短,没有以导师的面目评判冷寂的现实,我们在这首诗看到了作者难以抑制的心酸、心疼。世界很大,角落很多,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见大世界的姹紫嫣红,看不见角落里的期盼和渴望,我们的心真的能安宁吗?局限可以让我们习惯心安理得,但不能禁闭我们的思考。
孜格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那么成熟,但孜格写诗一定是有他的规矩。孜格的规矩就是所见、所思、所指尊崇内心的拷问,如《长尾巴的名字》《小满,刚刚合适》《枯荷》《石土豆》等,这些诗都有作者独特的审视。
《太阳云与绿皮火车》即将付梓了。孜格依然还是很少出没并不少见的诗歌场合。他的工作很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对诗歌保持的应有的尊重。不赶场,不打堆,才会把弥其珍贵的时间用于自己有态度的写作。我知道他身边的人很多还不知道他写诗,写了很多诗,这个诗集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从编辑业务上讲,我并不赞同他这样以时间顺序的编辑方式,因为他收录的早年的诗歌与最近的写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从单一到繁复,从稚嫩到趋于成熟,一本诗集把好的都放在了后面。后来一想,这也是对的,“不悔少作”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在孜格这里,写诗不是为了做一个诗人,而是为了拥有一份人生的诗意。这使我想到了俄罗斯诗人沃兹涅先斯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当一个诗人?”他的回答是:“我可以不去做一个诗人,但是有谁能够忍受住那被门缝夹住的一缕光的尖叫。”做不做诗人是一回事,能不能发现和抓住稍纵即逝的诗意,是另外一回事,我以为这就叫态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对诗歌的尊重。
是为序。
(《太阳云与绿皮火车》,孜格著,南方出版社,2024年2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