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金兰
涂拥自2015年重拾笔墨以来,便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考,构建了一个充满哲思与情感的诗意世界。在最新出版的诗集《河流上的诗歌微澜》中,诗人以短诗形式,呈现对自然、动物、工业遗存以及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思考与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
涂拥诗歌的动人之处,不仅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捕捉,更在于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这些诗歌,凸显出一种内与外的相互凝视,也让我们看到诗人“道德内省”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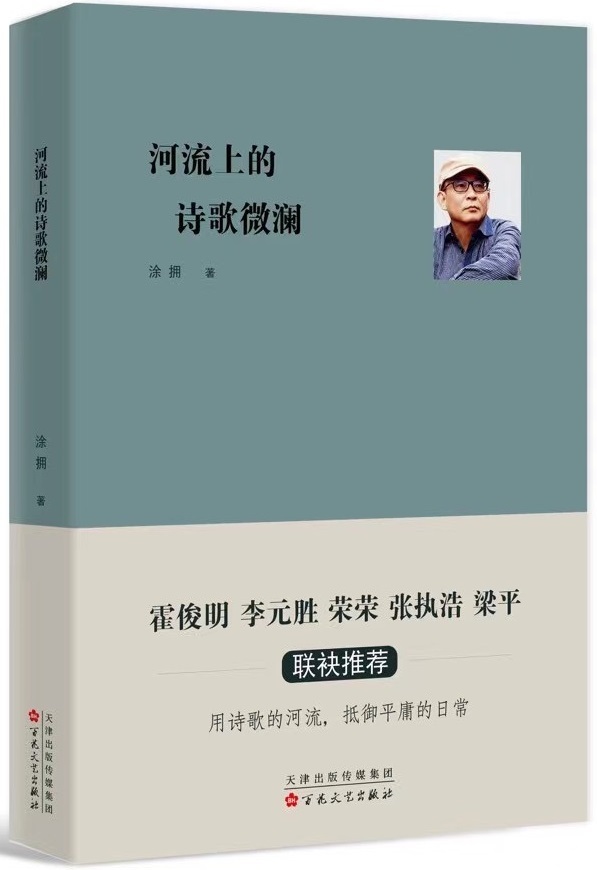
罗素指出,在现代哲学的技术世界观中,“人”被视作可以任意操纵的“物”。确实,我们都深陷其中。而诗人可以从一首诗中,将自己短暂拔出。这是诗人之幸。
涂拥善于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感悟力,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情感的微妙变化,以及时间的流转与记忆的沉淀,并将它们转化为内敛的诗意。
在《长江从家门前流过》这一辑中,呈现了诗人与父母、子女、爱人、友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并以“我”为中心点,向外辐射。
在《过程》一诗中,诗人以时间的通道为背景,细腻刻画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距离感和情感的交流。这种距离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隔阂,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深刻。“即便不说话,就可以站成地老天荒”,沉默中蕴含深情和默契。
《魔镜慧眼》一诗,则以一种幽默而略带讽刺的笔触,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诗人对“魔镜慧眼”这个名称的着迷,反映了对科技力量的好奇与敬畏,也表达了对过度监控可能带来的隐私侵犯的担忧。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类面临的一种生存的战栗。
《我们》一诗,则以一种超然的视角,描绘了两个灵魂在喧嚣世界中的宁静相遇。诗人用“闹市中的塑像”来形容这种超脱,强调了在纷扰的生活中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性。
此外,《寂静ICU》《这人有病》《体检》《我看见了骨头》《骨病》等医院场所的反复出现,也在提醒着人们关注身体健康。
涂拥的诗在智性与感性的交融中,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和诗意的深度。诗歌,促使诗人通过审视自我与他人和外物的关系,重建自我身份和世界的秩序。从而完成个人的寻根之旅。
涂拥的诗歌具有显著的生态主义意识。他常常以动物为载体,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在《在湿地鸟类标本馆》中,诗人通过标本馆中的鸟儿,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和改造。诗中的鸟儿虽然形态逼真,但已失去生命,这种对比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自然界的无奈。
涂拥通过动物的视角,折射出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唤起读者对生命意义和人类行为的深刻反思。《蛙泳过后》一诗中,诗人以青蛙的视角,表达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笨拙与不适应。在《恐吓》中,通过麻雀对人类模仿猛兽的反应,揭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尴尬地位。
这种对自然界的向往和对人类社会的批判,贯穿于他的诸多作品中。如“也许在等待/树枝上再现一只鸟儿/带来桂花的香气”(《那不只是一只鸟》),“古树沧桑,白鹭不断新生/此处生与死/相隔不到十米,而我们/只是当作了风景”(《过古楠白鹭地》)等。
涂拥的诗,不经意地在自然中呈现出一种生死蜕变中的否定态度。在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成为对立的两个面。只有弱化人的控制性与参与性,才能将人与自然并置于“存在”中。
《落叶》一诗,诗人将山中落叶与城市落叶作了对比,前者在“土中慢慢腐烂”,后者“来不及找到根/就成为了垃圾/在天亮之前,被清理”。真切而深刻地道出城市人的精神处境——无根的飘荡。
可见,涂拥的生态主义并非简单地复归自然,而是对人类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反思。
先贤老子提出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而庄子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诠释:真实而自由。当人去除一身累赘置身自然中,即便一条荒芜的小路,也会折射出一种向上的意志力。
强烈的象征色彩,是涂拥诗歌的又一特色。
《暗河中仍有玻璃鱼》通过玻璃鱼这一意象,象征着在黑暗中依然保持透明和纯净的生命。诗中的玻璃鱼,虽然生活在暗河中,却依然“亮出肺腑”,这种对光明和纯洁的追求,反映诗人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信任与向往。
《野象谷》巧妙地将人工喂养的大象与野生大象并置,引发读者对自由与束缚的思考。《两只打火机》更是通过打火机的比喻,巧妙地展现爱情的复杂性。火焰与火苗的对抗,象征着爱情中的激情与平静,冲突与和谐。“看烟消云散/却始终放在手心/像一直跟随的爱情”,将爱情的永恒与日常用品的实用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使涂拥的诗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河流上的诗歌微澜》这部诗集,不仅是涂拥个人创作的回顾,也是当代诗歌中的一部佳作。
诗人对生活经验的挖掘,为诗构筑起坚实的根基,并为诗歌赋予独特的心灵气质。
涂拥的诗歌不仅是对现实的记录,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反思。反思,即意味着超前。如《新郊区》等作品反映了社会变迁和历史遗迹的消逝。诗人通过对比过去和现在,表达对传统和历史的尊重,也流露出对现代化进程中失去的某些东西的惋惜,颇具现实意义。
此外,涂拥的短诗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诗歌语言,既有口语的亲切,又有文学的典雅,使作品既有广泛的可读性,又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让读者与诗,在语言中自然而然地存在和相遇。
当下,有的诗人过度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忽略了诗歌本身的内核。语言的陌生化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捕捉到个我经验中,那具有独特品质的感受与不同众的感悟。诗歌内在的东西,才是核。
当下的诗歌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中年一代,沉稳内敛,追求深刻;年轻一代,如 90 后、00 后,更多对生活日常的絮叨、解构、戏谑,当然也有对时代的思考。
新奇的语言与丰富的想象,颇能带来阅读快感。他们似乎不过多追求诗歌的意义,或许这本身也是意义。拆解意义也好,复归意义也好,都是诗与诗人的担当。但诗歌从语言开始,不应止于语言,该有一种纵向的无限延伸。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我们对语言的驾驭和理解,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范围。
当然,新诗的表达没有固定标准,充满诸多可能性。我们的写作都是一种尝试与探索。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波德里亚认为,诗歌的价值正是“诗歌是语言反抗自身法则的起义”。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诗歌是从对语言的反抗开始。反抗并非脱离,而是与顺从相对。诗歌还得依附于语言,但是不能顺从语言。诗歌在试图构建一种“破碎的完整性”,而语言与诗歌互证了其价值。
(《河流上的诗歌微澜》,涂拥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
作者简介
夏金兰,笔名夏泱,四川遂宁人,文学硕士,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四川省作协会员。诗歌、评论作品散见于《当代》《诗刊》《星星》《诗潮》《草堂》《诗歌月刊》《四川文学》等。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