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曾去长沙铜官窑,参观那个唐代时期的民窑,里面的瓶瓶罐罐上,刻有大量诗歌,都是窑工所作。顺录二首,其一:“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其二:“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想起这个,是因为在这个冬日的上午,望着窗外乌黑的天,突然想到“时空”这个词。上面的两首诗,正是时空的颜色。同时也因为,刚读过向萌的诗歌,从而感慨:作为诗人,不论古往还是今来,其实都是在岁月深处,他们注目的,是不被世人所关切的,他们咏唱的,是不被世人所命名的。即便昂扬,也在低处——那是光阴流淌的位置,也是命运交付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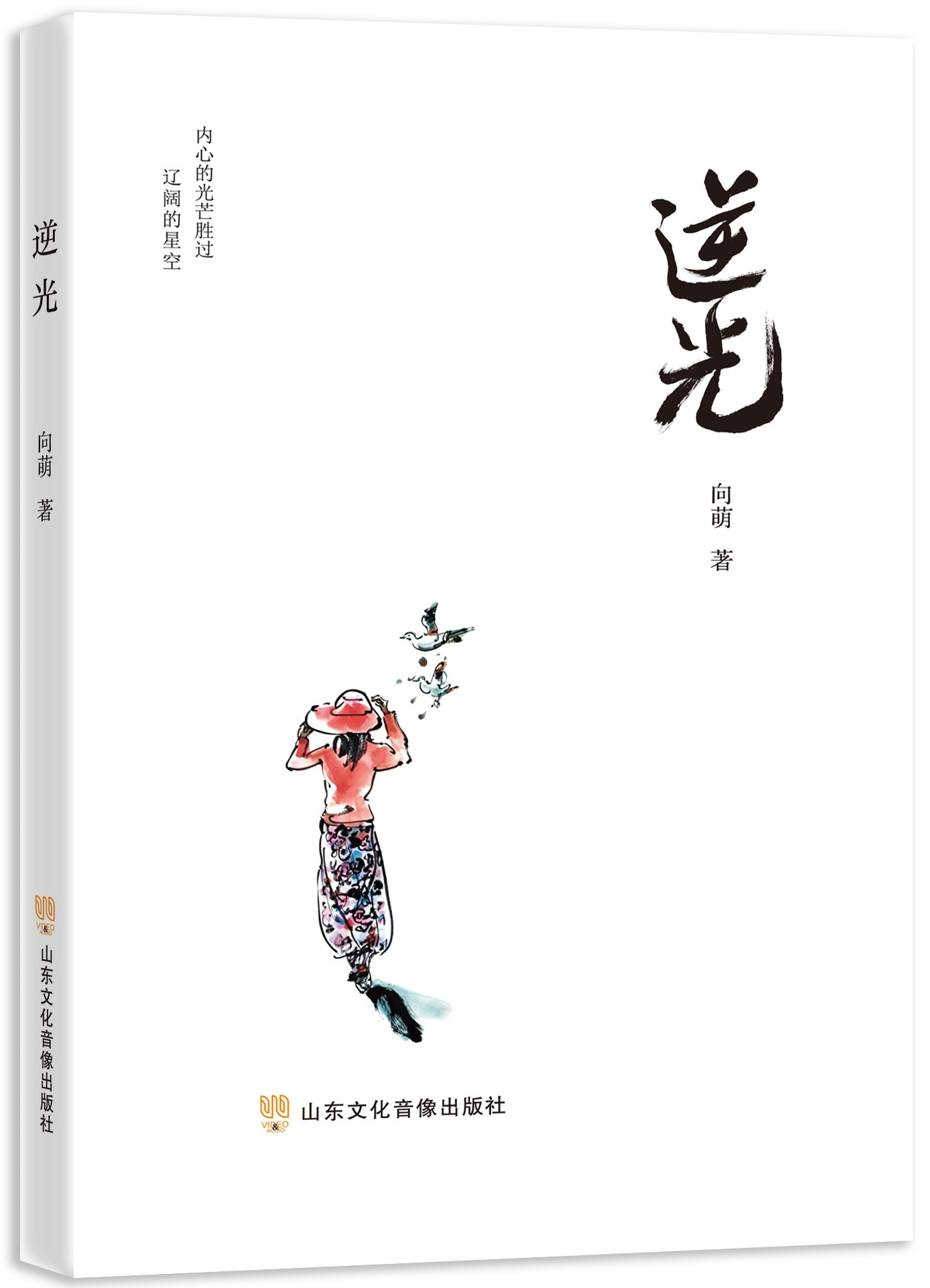
向萌是我故乡的诗人,我读她的作品很早,当时就惊异,为一颗灵异的心。那些原本熟悉的物事,被她重新发现和书写。“发现”是写作者的天职,一棵树在家门前长了数十年,如果你与它没有过对话,更没体察过它所接纳和承受的寒来暑往、风晨雨夕,它在你这里就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应,你在它那里也不存在。
而生命与生命,如同河流与河流,彼此相认和交汇,才能形成浩荡大川。我们之所以褊狭和局促,就因为不愿也没能力打开自己,并毫不迟疑地高估自己。对那些平凡里的卓绝,纤弱里的强劲,卑微里的巍峨,视而不见,也不想承认。
向萌在这方面是优秀的。她的诗从眼睛启程,她看见的,也是我们看见的,但她还用双手赋予体温,用情思赋予远景。即是说,她书写的对象,在身边,她表达的旨意,在深处。因为在身边,所以及物,而且谦逊地隐含着难度。深处可能是梦想,也可能是自我要求,还可能是高于自我的准绳。
人的一生,在现实世界里喜乐哀愁,这是自然的,人都是这样过的。但人的格局,则要看在内在星空里,是否给非现实的因素留下了位置。
再善于隐藏自己的作家和诗人,都无法在文字里真正隐藏自己,这是文字的坦诚和神秘之处。向萌在好几首诗里,都用了雪花的意象,这是她对自我的期许。但其实她不止于此。雪花的洁白、晶莹和春暖时归于无形,虽是一种好,也是一种轻,而向萌有重的一面。或者说,有稳定支撑的内核,否则写不出《一只被屠宰的羊》。
我经常爱提到刘文典教授的那句话。学生问刘教授作文的方法,他总是说:“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观世音菩萨,分解开来,是观世情,听民声,有一副菩萨心肠。民声之“民”,不仅指人,还指世间所有的生命。对生命的观照,是文学的灵魂,也是向萌注入诗歌的灵魂。
向萌之重,还体现在她现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许多事,公家事和公益事,她热心热肠,亲身介入。她不仅有感受力和审美力,还有行动力。这从她的诗里也是能观察到的。
我一直认为,向萌应该而且能写出更好的诗——如果她退到远一些的地方。但我从不这样对她说,我深知,对一个地方而言,如向萌这样的人是多么珍贵。
记得刚读到向萌诗歌的时候,我见人就问知不知道向萌。后来,认识了她,觉得听说的已是可喜可爱,见到后更觉可喜可爱。她聪明而且坚定。聪明的人很多,坚定的人很少,聪明而且坚定的人尤其少。她是一个好诗人,也是一个好人,我是指在真正的“人”的意义上去定义的人。这样的人,注定会成为增光者。
回到前面说到的长沙铜官窑,那些窑工和作家诗人一样,都是手工劳动者。他们的心事,因为书写而成为历史,成为文明的一部分,并终有一天与我们相遇。向萌的诗歌,但愿也是。
(《逆光》,向萌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25年1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