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浩
龚学敏诗集《白雪与挽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老主题、老题材如何在新的生活背景下复活?如何焕发生机?诗歌艺术领域的老树如何焕发新的生机?这实际上关联出新诗领域要面对并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脉融合问题。无论传统题材还是传统诗学,都需要在现代生活经验中承续与发展。
当前,写作的碎片化和个人化特征明显,带来阅读的困难,缺少情感的共鸣。《白雪与挽歌》是对英烈的歌颂、缅怀和祭拜的挽歌,这是一个严肃甚至是庄重的主题,也是一个老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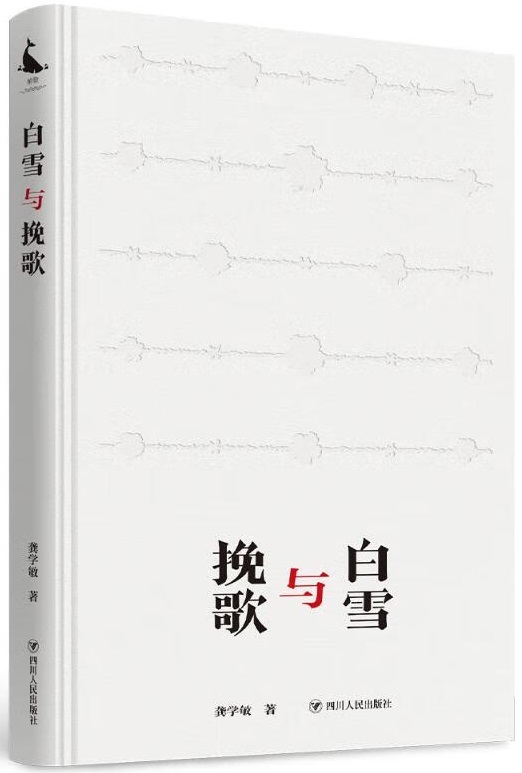
从难度上说,一是时空错位和生活内容的体验错位。写作者和写作对象之间具有时间空间距离、时代生活内容的隔阂性。在时间上存在80年的跨度,战争年代和长期的和平生活之间具有几代人心理体验的隔膜换代感;在空间上,作者长期生活在西南温润环境中,而写作的内容是东北的极寒之地,也相差极大。
另一个难度是创新的难度,对抗日英烈的挽歌这样庄重宏大的主题,诗歌史上已经有很多年、很多代人的写作,很容易陷入概念化的窠臼。要避免重复和创新很难,而且在表达上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性,个人化的发挥也很难。
本诗集的突破,在于以情感性、个人性奠定诗歌写作基础,营造出代入感,带动诗集在艺术上的起飞。诗集的核心在于真,老主题、大主题中的个人真,真实真诚。博大的爱与个人生活的结合,使诗歌境界宏大而细腻。
诗歌情感真挚强烈,以真实的个人认知经验和情感为驱动。开篇的《赵一曼》里,对于囚禁于监狱中经受酷刑的赵一曼来说,一方面是传奇性的人与事,另一方面也有监狱环境和内容的雷同化限制。
“驭雪成马,风是我刺向侵略者的长刀……刃是走在前面的那片雪”“万千的雪片是我用自由且纤细的手/磨出的刃。我用红色的火/奔跑。信仰所至,遍野都是/我的名字/都是我刀刃的名字”,诗歌以监禁中向外望的视角,寄情于寒风和雪片,驾驭不受限制的风雪驰骋万里,化身为战斗的豪情,豪迈的战斗精神充盈天地。
对于酷刑并不随意夸张化表现,“把指甲拔去吧,掉在地上,这样/我就把大地抓得更紧”“把牙齿拔去吧,天上一些,地上一些/让我将泼天盖地的仇恨咬得更狠一些”,以意志力化酷刑折磨为战斗的想象,既有贴切的细节吻合度和代入感,更表达出诗歌的力度。
“宁儿是遍地的月光。我朝着哪里/唱摇篮曲/哪里就是抚摸你的手”,穿着的红衣、纤细的手、对孩子的挂念,这些温柔的情感、外表的美丽,都是以日常化、生活化女性身份的贴切经验,真实而细腻地复活场景,更将爱与恨、温柔与豪迈、酷刑与意志之间强大的反差张力,营造出诗歌的力量感。
又如《杨靖宇》中,“风,用机翼的刀/把天空刮得比空坛子还干净……此刻,将军怀揣的黎明/正在被篦子一样密集的刺刀,一步步逼近”,刮空坛子、篦篦子,这些熟悉而温馨的江南化的日常生活意象,带来场景融入感,也为英雄的壮烈行为带来反差感。这是在日常化意象观照和融合理解下的抗战史、英雄史的重写、重述。
想象的丰富、内容的贴切,消除了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真实的情感与个人经验熔铸代入感带动场景的营造、想象的飞扬和奇崛的创造,并不突兀生硬,情感的共鸣真实自然。
对于成熟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想象的丰富、修辞技术的使用并不难,真实真诚这看似起点性的东西反而成为写作的难度。正因如此,《白雪与挽歌》的个人性、真实性、代入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其技术性腾飞的基础,合起来成为摆脱主题性写作中同质化的关键。
《白雪与挽歌》将形式美学与意义美学并飞,融合推进,在诗歌传统艺术形式的新旧融合中实现文脉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发展。
《十二烈士山》每节开头以“战士××倒下”复沓,12名战士的牺牲逐一分节叙述,节内分别集中于雪、桦树的泪、阳光、雨、土地、被子、树叶、石碑、刀、鸟鸣、雪、松树等核心意象,在排比复沓中错落有致,情感逐层递进,万物调动、万物交响形成各种合奏协奏曲。情绪的铺排推进如潮水般叠浪推进,既形成史诗般的场面感和过程性,又具有逐浪高的史诗吟唱感。终章合奏:“小孤山长成十二烈士山。一座新来的山/鸟瞰原野”“他们的姓名排成十二个月,用每刻时间/簇拥祖国的版图”,在轰鸣中再上高潮。
《魏拯民》在第一小节以“密营饿了”“粮食饿了”复沓推进至“饥饿在饥饿中昏迷”“连饥饿自己都饿了”,在第二小节转至“冬天来临”复沓。《金锦女》在第一小节以“有活着的吗”的问答体复沓,在第二小节变奏,转至“一只小百灵,用少年中国的嫩绿/飞过森林”复沓。均是排比递进,音韵与剧情性过程性同步铺开,使全诗格局宏大,山河环响,轰鸣不止,有歌剧性风采。
分节歌强化了诗歌的抒情节奏,情感推进更具层次。分节间的呼应与问答中的张力,不仅贴近民间歌谣的传统结构,也增强了叙述的互动感与现场感,历史记忆在复沓与变奏中获得回响。
这种形式选择并非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是与主题情感相契的整体构造,使庄严与哀婉、个体与集体在音律流转中达成平衡,进一步深化了诗意的真实与厚度,也形成史诗性美学风格。
庄严肃穆的主题与大量的个人化、日常化经验结合,抒真情;化用民歌、赋体等传统文化成分,诗歌内容与节奏结合,形神相谐,在对熟悉的审美形式回归中又创新创造,在现代白话诗诗歌三美建设中进行新的实践。
《白雪与挽歌》以有意味的形式反推意义的表达、情感的张扬,以形式凝聚意味,放大意味,形式和意味同步推进。
回归诗歌的源头,即源自个人化、生活化经验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达成可理解的艺术想象,在表达性和交流性之间达成传统诗学与现代经验的彼此消化。
新诗的发展始终要面对并处理和旧诗、传统文脉的断裂与传承发展的问题,《白雪与挽歌》的探索让人想起一首《插秧歌》:“低头便见水中天,后退原来是向前。”
(《白雪与挽歌》,龚学敏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