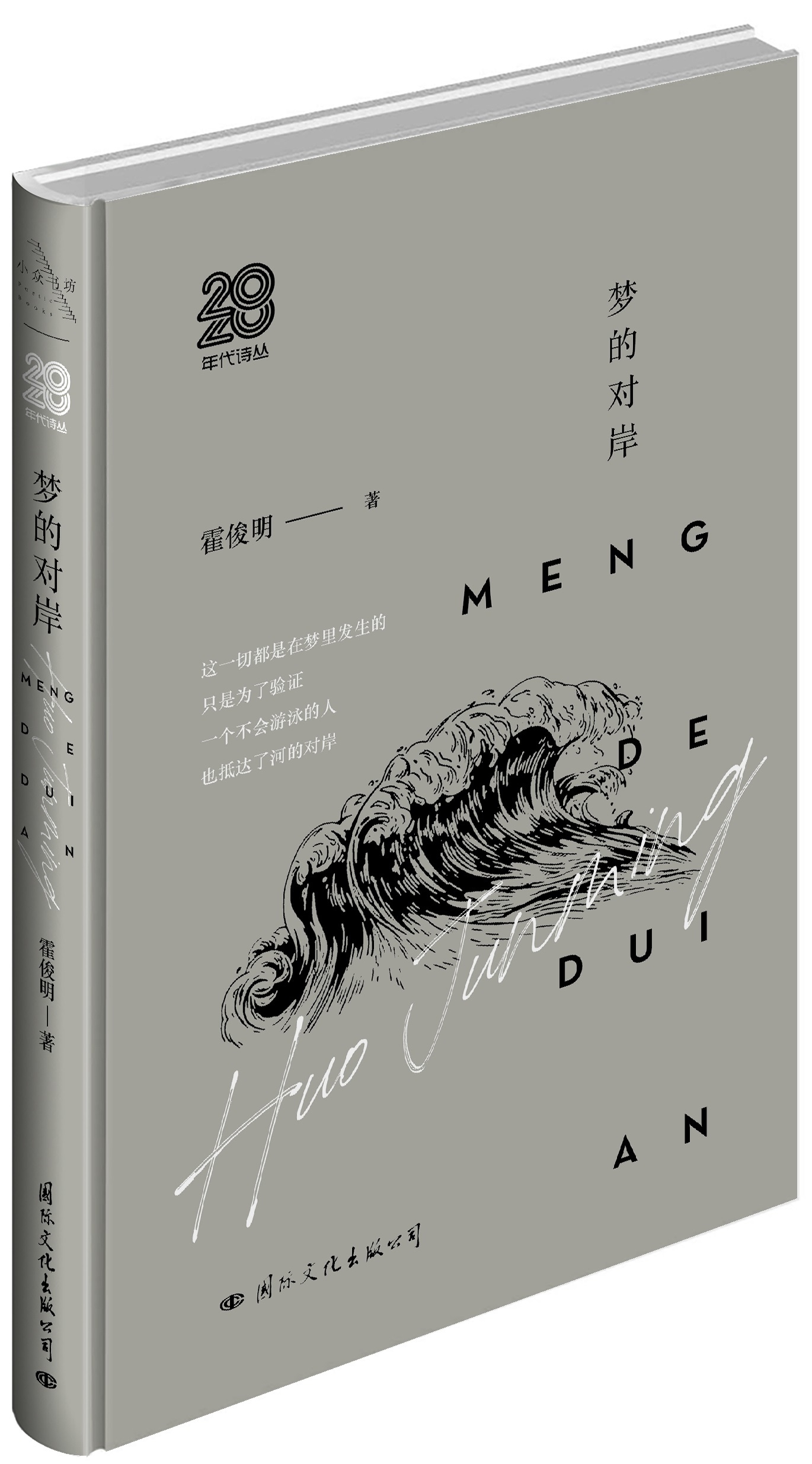
薛菲
本雅明在《单行道<建议用这样的“栽培”来保护公众>》一文中说:“评论和翻译对于文本宛如风格和模仿对于自然:它们都是用不同方式看待对象的产物。对于神圣文本之树,二者只不过是永远沙沙作响的树叶,而对于平庸文本之树,它们则是适时落下的果实。”作为“树叶”的其中一片,梳理出一条隐秘的线索,尝试求证“对岸”的可能性,也是“树叶”趋近于“果实”的可能。收录诗集中的102首诗,是否是一艘摆渡至对岸的船?
《梦的对岸》是评论家、诗人霍俊明最新所著诗集,共分6辑,收入诗歌102首,是一部回忆之诗的总和。以读者的视角来看,除了深情与追忆,也是评论家身份外的一次深呼吸,一次刀刃向内的过程,一次彻底的释放。
第一辑“小地方的笨拙笔记”收入12首,以“笔记”为小标题,作为一册诗集的开头,强调这样的重要意义“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现实感’的诗歌写作”(霍俊明《无能的右手<“下槐镇”离中国现实有多远>》),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诗人正在践行的写作关怀和生命向度。
第二辑“高原的土红色封皮”收入26首诗,“高原”通过阅读可以得知并非一处确切的地域,但代表着人类精神生存的典型。高是地理位置,土红色是近乎于生命本质的色彩。是诗人的游历之地,心绪和缓,笔触延伸至心灵的境地。
第三辑“松针上行走的隐士”含16首诗,每一首都指涉形而上的意味,有趣,甚至在看似轻松的诉说中,有年代感和牢牢把握节奏的举重若轻。
第四辑收入18首诗,“彼岸花或沙漏现世”充满硬朗的隐喻,或者说是确定的宿命感。
第五辑“纸上的云山与大象”,收入的12首诗厚实中透着轻逸的调子。
第六辑“响水桥笔记”与第一辑一样,回溯生命之源,是对源头的反思与触抚,含17首诗。与第一辑不同之处在于直接写到回忆,与“响水桥”的明亮相对,并非是轻松的,但有海的气韵。
不同于当前诗歌写作中的乡土想象或苦难经验,诗人要打破恰是类似的表面化、程式化所引发的诗的无效性,是一股想要在沉默中说些什么的冲动。如果单从字面意思解读,梦的对岸有醒来或清醒的意思。对照诗集来看,的确有这种意味,并非抽象,虚无缥缈,都是沉甸甸、充满现实思考与历史观照的诗。
那么,也不必反过来,问梦是什么,或者陷入到此岸至彼岸的虚幻旅程。行动的意愿来自对无效抒写引发沉默的破局行为,从而宣布“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也抵达了河的对岸”。浅显的阅读很容易陷入类似的误区,即远离故土恍如隔世或纸上的返乡,将不会游泳的人依据字面意思理解为自然而然的返乡之举。
通过一些访谈资料,笔者了解到评论与诗都是霍俊明一直以来的热爱与坚持。诗使诗人直面生存的本质与境况,结合这一点,梦的对岸也容易使人理解为一种徒劳,西西弗斯似的行为。直面时间深入现实的写作者,大概都面临着推石上山者的悲怆与倔强。
在梦的对岸,不同地貌、地域、场景、人物中的无数次逡巡,诗人寻找到了什么?《白鹭辞典》中这样写道:
黑色的啄
消失在阴影里
更多的时候它们静止
只在短暂的繁殖期
它们才谨慎地张开喉咙
发出任何乐器
都不能模仿的声音
它们更喜欢独自起飞
像一块快速移动的白雾
波德莱尔的时代,诗人对城市的鞭挞是一种精神谴责。现代语境下,诗人在层出不穷的丧失与光怪陆离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黑色的啄/消失在阴影里/更多的时候它们静止”。“白鹭”与其说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不如说是无形体、无意识、无声无臭形同空气一般的无奈与缄默。
那么,诗人又为何在诗集命名中给出“对岸”这个确切的地址,并启示一种抵达?现代语境下,现实生存离鸟语花香、充满所谓诗情画意的画面相去甚远,诗人在诗中始终清醒、自持,始终超越着“拈花微笑”式的释然,却又徘徊再三,不忍离去。
这使得诗的思考与环境处于类似于沉默的尴尬。茫然四顾,“抵达”或许又是新的开始。“没有水流声,也没有/拍打水的声音/一切都悄无声息”,这三行诗让我们从默片时代卓别林戏剧迅速过渡到等待戈多的荒诞,以及萨特“他人就是地狱”的哲学论断。“这一切都是在梦里发生的”,使荒诞和无意义再进一步,直接揭示生存本质的惊悚与荒诞。
一个陌生人
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你只能
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
像是做了一件亏心事
小心翼翼
还有几分歉意
你不能超过他
路太窄了
上面尽是陌生人
以及深灰色的影子
这个下午
陌生人
也更像是幽灵
——《陌生人》
诗人将颇具哲学意味的论断置入诗中,以日常的面目出现,但是达到了所要传递的效果。类似的诗还有《皮影头茬皮影身》《一个人从云南回来后》《一位脱口秀老乡》等诗。因为看得透彻,读罢这些诗,等回过神来,真有“钟摆静止/世事如烟缕”(《响水桥杂谈》)之感。时间不过是“静止的艺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传奇时代的绝响与消失。
《异人传》这首诗,作者描写祖上异人霍二先生“目光如炬/夜间能见异物”。人物已随着时代的巨大变迁成为集体的缄默或秘密。将之写下,是见证,也是挽留。在此前或此后的时代里,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接受着如此深信不疑的注视。
怅惘的视线中,一缕温情来自《生日及次日遇两场春雪有感》。三月春时,乍暖还寒,诗人的生日是个好日子,连积雪都是“嘎吱嘎吱的响声/多像年轻人的好牙齿”:
谈到雪
我和妈妈都很开心
不再像多年前
担心倒春寒
不再担心粮食和蔬菜
说到这里会发现,诗人所谓的“对岸”与“梦”是否是颠倒了次序?充满回忆性的场景反而成为对岸,而身在其中却时时有梦中人之感。生存的荒诞性,仅仅四个字就反映出来。却成为冷峻而有效的语言,成为打破沉默的时刻。为诗集写序的诗人雷平阳清楚地点出:“这本诗集是霍俊明令人惊叹的大批量诗评文字之外的大海尽头的海岬,亦可视为汪洋中的一条条沉船。”(雷平阳 代序《现况与幻觉》)这可视为诗集在情感上的旨归。
艺术追求方面,诗集秉承着霍俊明诗歌一贯在冷峻之外的温情。出版于2016年的诗集《怀雪》,就已初见端倪。这部号称“没有目录的诗歌文本”共收录100首诗。细读《梦的对岸》或《怀雪》,自始至终都有对终极意义的凝视。这凝视或眼神如果有时间段,它是黄昏的,精准地说,是暮色的:
他再一次独享了暮色
茫茫夜色里
一只水鸟独立于栀子花头
他模仿古人造句:栀子花栖夜鸟寒
这样的句子,总是让我想起行走于批评与诗两条“交叉小径”上的诗人,他的上下求索与苦苦追寻。同为诗人的雷平阳很理解这一点,并于阅读后写下诗一般感性的体味:“而霍俊明的身份、骨相、血液的浓度和眼界更是我所留心的——将事实导向未知与神示,为虚无赋形并产生公论,霍俊明的个体总是同时迸发两个人以上的力量、意志、智识,而且事件的陈述不是基于结局,而是基于世界就此铺开。”
“世界就此铺开”这一条显豁的道路,是否就是“梦的对岸”?“墓地上的阳光并不是在眷顾死者”,阅读霍俊明的诗,仿佛身处一个闪电的季节,其实是走在诗人笔下的一场又一场洁白的大雪中,我们不过都是时间的过客。
“‘历史’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已经了无踪迹了,更多的时候被患健忘症的人们抛在了灰烟四起的城市街道上。”(霍俊明《“下槐镇”离中国现实有多远》)这里的历史,指一种现实想象,“过客永远是过客”(李南《下槐镇的一天》)使得诗人写下的诗,像掩藏着叹息和巨大秘密的谜底。然而,还是让我们和诗人一起乐观而坚定,相信诗对世界的“验证”,已抵达了“河的对岸”。
《梦的对岸》,是一次给出地址的寻找之旅。目睹刀刃向内,聆听虚空的浩瀚之声如同身处林海雪原。《梦的对岸》与其他诗集不同之处在于:不配合常规回忆的姿态,不原谅造成失去与变迁的倔强表情,不苟同一棵生长在旷野的树却开满虚荣的花朵。
这是一部干净得充满尘埃,悲伤得溢出微笑,沉默得充满歌唱的诗集。
参考文献
[德]瓦尔特·本雅明,王涌译,《单行道》,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德]海德格尔著,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意]维柯著,新科学[M],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霍俊明,《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霍俊明,《梦的对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2年版
霍俊明,《怀雪》,黄山书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
薛菲,文学硕士,甘肃甘南人,现居新疆伊犁。伊犁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伊犁师范大学伊犁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作品散见于《星星》《伊犁河》《扬子江》《诗潮》《诗歌月刊》《西部》等文学期刊和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诗合集《在甘南》。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