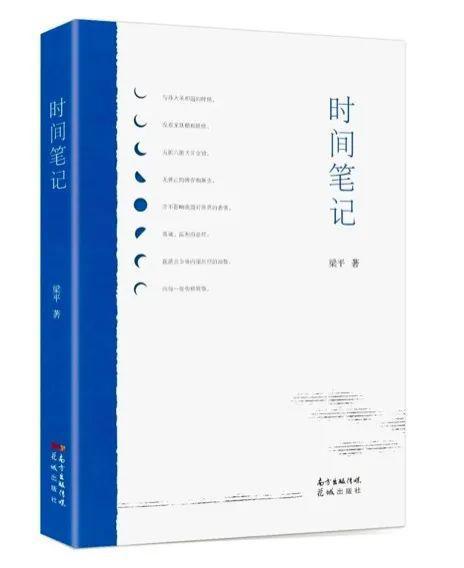
纳兰/文
时间的每一时刻,每一秒钟都是“救世主可以由之通过的狭窄的门”(本雅明《历史哲学论文集》)。任意时间和所有时间、片段和整体,时间并不构成任何障碍,换句话说,谁能从时间的窄门里侧身而过,谁就获得了“永生”。而时间的言说就等同于拥有,那是一种富足的语言,而非“贫乏的语言”。改造语言是为了接近神性。改造语言是为了恢复“要有光”般的言说的有效性。
耿占春先生在给诗人梁平的《时间笔记》所写的序言中提到“治疗型的语言”,这就是一个人将身体和“某种话语形态”之中隐匿的弥赛亚力量显现出来的时刻,即“治疗的语言”,“治疗的思想”。梁平的《时间笔记》记录的是他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或可看作是他在某一时刻,某一秒钟他的思想先于身体通过了“时间的窄门”所获得的启示、彻悟,这种启示或彻悟,有获得救赎的快感。
在《时间上的米沃什》一诗中,梁平写到:“以鲜血分行救赎历史。敏锐、毫不妥协地承担,/撕开人类剧烈冲突中的赤裸,/在时间之上。”我被“以鲜血分行救赎历史”这样的诗句所震撼到,这不仅是“诗的见证”,还有一份担当,有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绝。诗人梁平既是在以一种“批评意识”对米沃什深度理解和阐释,也是一幅他自己的精神的自画像;他的“批评思维”与自身的诗思维有种本质的等值,也与米沃什的诗思维有等值,用乔治·布莱的话说,就是“因此,诗人的兄弟和第二个我,即批评家、读者,就是在其身上重复诗人的某种精神状态的那个人”,在波德莱尔看来,伟大的艺术家是些富有想象力的人,而富有想象力的人则是用他们的“精神来照亮事物,并将其反光投射到另一些精神上去”的人。诗人梁平也是将自己的精神的反光投射到了另一些精神上去的人之一,他与米沃什精神上彼此照亮,责任和使命重合,他找到了《时间上的米沃什》,“可以用时间制造画面和记忆,/并赋予它庞杂寓意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梁平也在自己的《时间笔记》里,“制造画面和记忆”,而自身也成为了“时间上的梁平”。“每一个时刻都有斧凿的痕迹”,这既是米沃什,又是梁平在时间的身上寻找拯救的出口,米沃什时间笔记里的“惶恐、困惑、悲伤和虚无”,梁平也亲历了一遍。
在《我被我自己掩盖》这首诗中,他分别写到了我被一本书、一个梦、一句话掩盖,最终说出了“我被我自己掩盖”。“书、梦、一句话”,这些处于心理学的无意识领域、“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现实世界所带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处于以赛亚·柏林所说的,不受人干涉的“消极自由”的层面,即“在这种意义上,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我被掩盖”与人无尤,它绝非是道德的或美学的困境,而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受困,既有“草堂的荒草爬满额头”的忧愁,又有“我看见和我看不见的,/都不能指认”的痛苦,被“掩盖”的解救之道是“在城市进入深睡眠以后,/我的另一个我,游离,/我的灵魂出窍”。“我就是埋伏的天狼星,/在天上看,看城市揭开面膜,/看赤裸裸的人。”(《城市的深睡眠》),这是从诗学的天空俯视“下界的伦理”。
我的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
但不是行尸走肉,过眼的云烟
——辨认,点到为止。
——《欲望》
梁平的《欲望》之诗,其关键词在于欲望的“减少”和“清空”,并没有如柏林所说的那样:“我必须自己从那些我知道根本无法实现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疆域的主人。但是我的疆界漫长而不安全,因此,我缩短这些界线以缩小或消除脆弱的部分。”梁平不仅没有显示“脆弱的部分”,也没有“战略性的退却”,退回至理性和灵魂的“内在城堡”,而是“读懂了时间。星星、睡莲、夜来香”,“我和窗外的鸟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他和这世界处于一种对话般的关系之中,处于一种物我合一之中;他和世界处于一种观看和倾听之中,但不是近距离地触摸,“以最简单的方式,适当的距离,/安静地观察这个世界。”(《一只简单的母鹿》)。在“我的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的清空状态下,达到了“醒悟之后,行走身轻如燕”的化境。梁平有随时间而来的智慧,正如《耳顺》所写:“耳顺能够接纳各种声音,从低音炮到海豚音……以后任何角落冒出的杂音,/都可以婉转,动听。”原本声音是“浸淫久了,小夜曲每个节拍,/都在凌迟我的身体”这般的痛苦与不可忍受,“凌迟”之感如今变作了“皆可入心入耳”,“耳顺”连带着将打通的观感变为眼顺、心顺。耳顺是一种“我通过放弃上路来克服道路上的障碍;我退回我自己的教派、我自己的计划经济、我自己苦心经营的孤岛中,在那里没有一种外界的声音需要倾听,没有一种外在的强力可以产生影响”的智慧。耳顺、眼顺和心顺,加以“净心、净身、净念”(《免疫力》),他已经达于身心安然之境。他不仅有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他亦参他的禅“如是是不是柳如是,/如是的庵是不是真的有庵”(《相安无事》,)亦有随觉悟而来的菩提心,这种觉悟是“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这种“不二法门”,比如“随心所欲,所不欲。”(《私人档案》),“舍了的,可以得,可以不得”(《舍与得》)。
诚如梁平在《十字路口》所说:“我的文字,和我一样桀骜,/积攒了一生的气血,/咄咄逼人”,他的诗是“气血之诗”,是“以鲜血分行救赎历史”的大诗。写诗就是他在一张纸上输入“一生健全的档案”(《一张纸上》),一张纸上就是眠床,一首诗就是“隐秘的修行”。从《别处》中的“别处被我一一指认。”到《墓志铭》的“同名同姓成千上万,只有你,/能够指认,而且万无一失”。“我叫梁平,省略了履历”,他完成了一次对世俗世界的辨认,对“天地之独往来”的精神之我的指认。从辨认到指认,是笔记对时间的确认,是灵魂对得到救赎之道的确认,是诗对诗人的确认。
从《时间笔记》到《私人档案》,是从笔记到心迹的自我刻画与书写,是对“那套种植的手艺,横竖撇捺”的执念于挚爱。在“有些话可以不说”与“有些事可以不做”之间,是对“可说”与“可做”的了然于心,是“不逾矩”的自由。“有些话可以不说,/时间久了,话就化了”,这是诗人对语言的持守和沉默的信任,也是深信时间对“坚硬语言和心灵”有软化的力量。“话就化了”是穿透时间的语言裹挟着一颗柔软的心灵。读梁平的《时间笔记》,是一次从时间中斧凿出一个拯救的出口的尝试,在他的诗中呈现的是一个面目清晰,爱憎分明的诗人形象。“时间堆积,如同著作等身”(《花名册》),这是诗人用纸折叠的一个沙漏,其中装满了词语的沙粒。在时间和著作的双重作用下,诗人在时间和诗中,留下了自己的清晰的印记。

本文刊于7月3日四川日报第11版、文艺评论版《原上草》。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川观网友23224 2020-07-03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