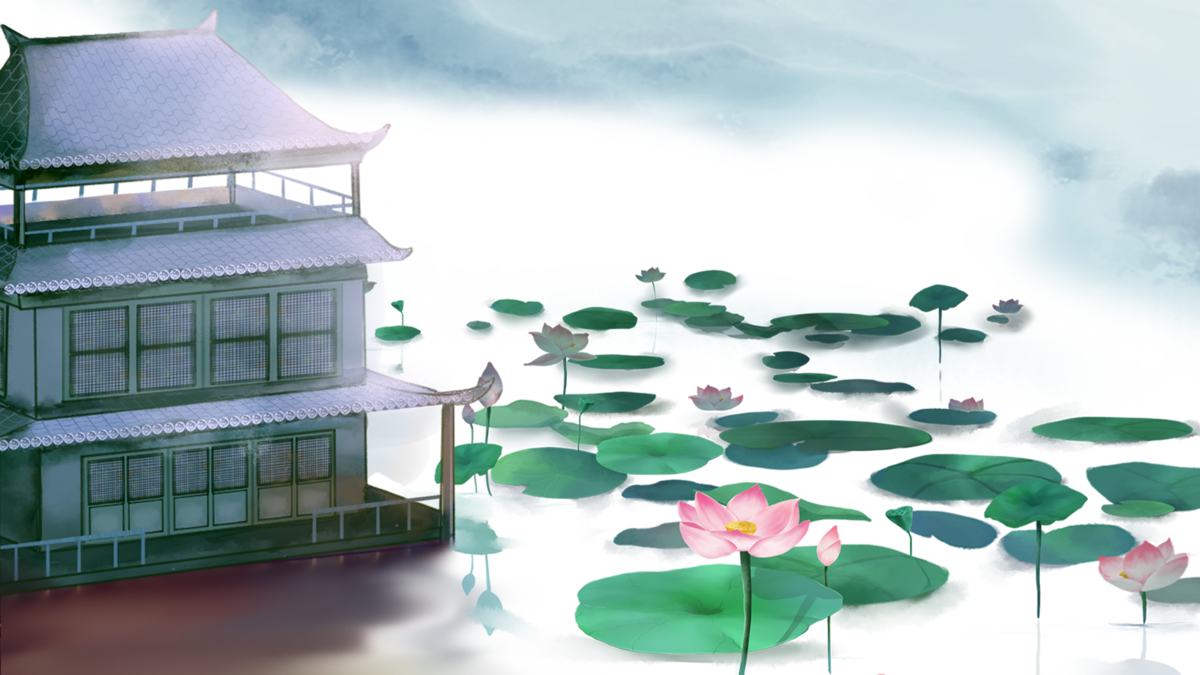
文/瑞晶
春打五九尽、春打六九头。
雪,化得差不多了,只有背阴的地方还能看得到几条白道儿。雪水又冻成冰的一滩滩、一块块。没有雪的呼兰河沿上,只有沾着雪水的黑土和枯草的干黄,河里的冰也变成了灰色,水浅的地方已经化开了一汪水,也是灰蓝色。晚上还是会下雪,不像冬天里的雪那样飘飘洒洒,而是湿哒哒、粘乎乎地倒了一地,这雪也是不用扫的,晌午的太阳一晃就化了。
虽然摘了帽子、围巾手套,棉袄棉裤还是脱不得的。小孩子出去疯跑一阵回来,背上全是汗。不知是久未洗澡,还是在草地上滚进了草叶子,只觉得从脖梗到后背都很痒,一个个走着走着东扭西蹭,忍不住就反背过手去抠两下,弯腰拱背的就像西岗公园里的歪脖子老榆树。实在够不着就像骡子一样在门框上蹭几下,汗消了也就忘了。
而我,偏偏受不了、忍不过。非得把线衣脱了翻过来细细找一遍,再让奶奶挠几下,重新穿回衣服才算好。奶奶一挠一边说:“春长喽……都说春天里的小孩儿和小树小草一样的往高里窜,长得太快了,皮紧了绷得痒。”奶奶把抖过的棉袄递给我,又说:“跟你爷一个样,后背沾不得半点痒。”
爷爷喜爱挠背,而且无论春夏秋冬,他的背好像特别爱痒。每天晚上都喊我帮他挠。他斜坐在炕沿上,我跪在他后面,先从右边肩甲骨下缘开始,再向上向左,除了右下腰那个拳头大小的疤瘌,其他地方都细细地挠几遍,我一边挠着一边听爷爷给我讲以前的事儿,听着听着手就停了,爷爷也不管,还是讲着,直到我的眼皮子打架。
一天下午,我跪在炕桌边写毛笔字,后院的阿焕站在墙头上喊我:“快走,西河沿跑冰排了”,我蹦下炕,还没穿上鞋,就被奶奶喊住了。家里是不许我去河沿的,只有端午节和元宵节,才能和大人一起去。夏天时曾趁家里没人的时候跑去过,却也不敢像其他孩子一样下河游泳,只是站在河沿上帮他们看衣服。现在春耕还没开始,大人们都闲在家里,想跑出去可没那么容易。见我半天没动静,阿焕一个人跑了,甩着她的两条刷子辫,她的头发又黑又硬,两条辫子直愣愣地在耳边支着。
阿焕是家里的老二,姐姐阿丽长得清秀高挑,她却像个假小子,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哑。平日里经常穿一条差腿裤,就是一条腿是红色带花的,另一条腿是旧军裤改的裤子。听奶奶说这是她妈想再生一个差样儿的,就是想要个儿子。
因为这裤子总有男同学笑她,从不见阿焕像其他女孩子一样,要么哭着回家要么骂几句,她直接扑上去就打,而且每次都打赢。她也一脸不在乎的,梗着扎两条刷子辫的头走了。
因为好打,她成了我们周围的孩子王,有时候也会像男生一样欺负女生。大家伙多少有些怕她,我也是。
看着阿焕跑远了,我蹭去厨房找吃的。奶奶正在做饭,从坛子里拿出萝卜缨子,抖掉上面的粗盐粒,冲洗了和豆腐炖。盐渍了一冬天的叶子,在锅里竟也是绿油油的。在这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也算是美味了。
奶奶递给我半截胡萝卜,打春之后,这胡萝卜也不像冬天里那样,脆甜的咬起来咔嚓响,咬一口吭嚓,也还甜。天还是不见暖,这些菜却都变了样。没吃完的冬储白菜和大葱,一下子变得蔫头耷脑,叶子全都干黄了。要是放在那几天,再切开看,里面竟发出了新的黄芽。这菜是没人再吃的。不管是土豆长了芽、萝卜发了叶、还是白菜冒了苔,人们统统都是不吃的,很嫌弃地直接倒在河沟里、粪堆上。就算只能啃咸菜嘎哒。
没什么菜可吃,只能吃些去年秋天晾下的干茄皮、豆角丝。而这些干菜又是极喜油的,杀年猪的肉早就吃完了。少油的干菜,盛出来后锅里一大圈白。
我家的下厢房里还有两坛猪油,油底下还埋着肥肉。加上爷爷三天两头磨豆子,用豆渣加上芥菜叶一起炒。并没有觉得苦春有多苦。倒是,常见大娘婶子们,雪化了就开始上山找野菜,只是一天下来也没啥收获,篮子里几棵歪头的响根蒜。
说是春天了,远远看着大地里泛着点绿,走过去细看尽是枯草,不见绿苗。那些小苗一个比一个藏得深,谁也不肯先出来。杨树和柳树看着变色了,也怎么都寻不见新芽。除非折根柳枝,能看到树皮下面泛着黄绿,这时候的柳枝却也没那么好折了,像皮条子样难扯断。
白天好像长了一点,家家户户还是早早地关上院门。
我跪在炕上给爷爷挠背,爷爷给我讲跑冰排的故事,他说跑冰排的声音轰隆隆像打雷、像火车过。他还看见过一匹白马,被冰排冲着向下游奔去。我不信,一定是他看错了,把大冰块看成了白马。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呼兰河里跑着冰排,每一块奔腾的冰块上都站着白色的马,那些马都长着冰做的翅膀,一起往下游飞。
第二天早上,躺在炕上听到西河沿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真的在跑冰排了。冰面鼓了,冰块冲着冰块向下游怒奔而去。
也不知道是哪天,听见了燕子叫。
棉袄是真的穿不住了。
也就几天没出去,丁香的叶子都长了半寸长,细细的青紫色。掐下来一叶,真苦。
胡同里的孩子们吹着柳条皮做的哨子,有的声音尖细、有的粗闷,那是因为柳条的粗细不同。我也跑去折柳枝,选一段光滑青皮,握在手里,左右手向相反方向一拧,树皮就脱骨了,拿小刀割下来了截,再轻轻地把哨口处的老皮刮掉一层,这样吹起来更响。
这柳哨声响过几天,就把春真的吹醒了。
春耕拖拉机黑天白夜地叫,直叫到白毛杨的白絮四处飞扬,地里也见了青苗。

本文刊于四川日报第23版、文艺副刊《原上草》版面。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